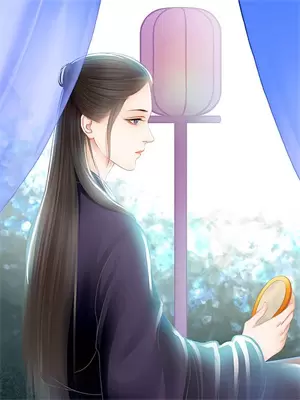冰冷的金属气味,消毒水挥之不去的刺鼻,
还有……死亡本身那难以言喻的、沉甸甸的凝滞感,是我每日呼吸的空气。
市局法医中心的地下二层,这里的时间流速仿佛与外界不同,
永远滞留在永恒的低温与寂静之中。无影灯惨白的光柱精准地投下,像舞台追光,
笼罩着不锈钢解剖台。台上,那个曾与我分享体温、呼吸和所有细碎日常的女人,
如今只是一具需要被解读的、沉默的证物。曾丽。我的橡胶手套边缘被指关节绷得死紧,
发出细微的、令人牙酸的咯吱声。金属器械托盘就在手边,
排列着冰冷而精确的工具——手术刀、骨剪、开颅锯……它们熟悉得像是我肢体的延伸。
目光掠过她颈项间那片触目惊心的青紫色扼痕,淤血深深嵌入皮肤纹理,如同邪恶的烙印。
窒息,这初步判断像钝刀割着神经。我拿起放大镜,凑近那片淤痕的边缘,
寻找任何可能被忽略的挣扎痕迹、指甲的划痕、或是一丝不属于她的纤维。指尖微微颤抖,
不是因为恐惧,而是某种更深沉、更接近本能的东西在撕扯。我强迫自己的视线向下移动,
落在她微微蜷曲的手指上。指甲修剪得圆润干净,
指缝里却嵌着一点极细微的、暗褐色的污渍。不是泥土,不是灰尘。
职业的直觉像冰冷的蛇信,瞬间舔舐过我的脊椎。我取来棉签和生理盐水,小心翼翼地,
屏住呼吸,如同对待最易碎的珍宝,将那点污渍刮取下来。
棉签尖端沾染上那抹不起眼的褐色。我将它放入无菌试管,贴上标签,动作近乎麻木的精确。
“常规毒物筛查加急,”我的声音在空旷的解剖室里响起,干涩得像砂纸摩擦,“还有,
这个……做菌群分析。”助手小张隔着口罩,眼神里掠过一丝不解,但还是点点头,
接过试管快步离开。厚重的气密门在他身后合拢,发出沉闷的“砰”的一声,隔绝了外界,
也仿佛将我彻底锁死在这个只有我和曾丽的空间里。寂静重新统治一切,
只剩下通风系统低沉的嗡鸣,像是地底巨兽压抑的呼吸。我摘下口罩,深深吸了一口气,
冰冷的空气刺痛肺叶,却无法驱散心头那团越来越浓重、越来越粘稠的迷雾。
目光重新落回她的脸上,死亡带走了血色,留下一种近乎透明的苍白,
却奇异地没有带走她眉宇间那种惯常的、带着点倔强的安宁。
昨夜……昨夜我们还在一起吃晚饭。她做的红烧排骨有点焦了,我笑着抱怨,
她佯装生气地戳我额头……那鲜活的笑语犹在耳边。手指无意识地抚过解剖台冰凉的边缘。
那件她送我的旧风衣,深灰色的,袖口有点磨损,昨天傍晚我脱下后,
就随意搭在了客厅的沙发扶手上。那熟悉的触感,
粗砺的斜纹面料……时间在绝对的寂静中流淌,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般漫长。
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橡胶手套下,指尖冰凉。不知过了多久,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
打破了死寂。气密门再次滑开,小张几乎是冲了进来,手里捏着刚打印出来的报告单,
他的眼神不再是疑惑,而是混合着震惊和难以置信的惶恐。“邓……邓老师!
”他的声音发颤,将报告单猛地递到我面前,纸页在空气中发出哗啦的声响,
“结果……出来了!”我接过那份薄薄的、此刻却重若千斤的纸张。
目光直接锁定在关键的数据栏上。血液毒理筛查:阴性。常规药物:阴性。
我的视线急切地向下移动,落在那项“未知残留物高精度质谱分析”的结果上。
7研发状态:预计上市时间——203X年当前时间:202X年环沙星三代?
XK-7?203X年?白炽灯光线仿佛瞬间变得无比刺眼,
报告单上的铅字在我眼前扭曲、跳动、融化。一股冰冷的寒流自脚底猛地窜起,
瞬间冻结了四肢百骸。十年后?这绝不可能!实验室污染?样本混淆?
任何一个念头都荒谬得如同天方夜谭。我的手指死死捏住报告单的边缘,
纸张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一股冰冷的麻痹感顺着脊椎向上蔓延,直抵大脑,
思维瞬间陷入一片空白和刺耳的嗡鸣。“邓老师?您……您没事吧?
”小张的声音像是隔着厚重的玻璃传来,充满了担忧。我猛地抬起头,视线锐利如刀,
刺向他:“监控!昨晚……中心大门、电梯、走廊、解剖室门口……所有的监控录像!
马上调出来!立刻!”我的声音嘶哑,带着一种自己都感到陌生的、近乎失控的急迫。
等待监控调取的时间,每一秒都如同在滚烫的油锅里煎熬。我像个困兽,
在解剖台前狭窄的空间里来回踱步,橡胶鞋底在光洁的地面上摩擦出焦躁的沙沙声。
曾丽安静地躺在那里,像一个巨大的、无声的质问。终于,小张带着一个加密硬盘回来了。
他动作麻利地连接上了解剖室角落那台用于记录解剖过程的电脑。屏幕亮起,
幽蓝的光映着我们两人紧绷的脸。冰冷的硬盘指示灯规律地闪烁,像某种倒计时的信号。
我一把夺过鼠标,手指因为用力而关节泛白,点开了第一个视频文件。
时间戳:昨晚十一点二十七分。画面是法医中心入口处的广角监控。深夜,
空旷的大厅只有惨白的灯光,值班警卫的身影在屏幕一角昏昏欲睡。毫无异常。电梯监控。
空无一人。数字缓慢跳动。走廊监控。长而幽深的通道,顶灯间隔投下昏黄的光圈,
寂静无声。除了我的身影——十一点四十分,我穿着便服,
手里提着那个该死的、装着宵夜和所谓“重要资料”的文件袋,脚步匆匆地走向解剖室方向。
我进去,门关上。时间一分一秒流逝。画面单调得令人窒息。“快进。”我的声音紧绷。
小张操作着。画面加速流动。凌晨一点零五分。解剖室的门,开了。
一个身影从里面闪了出来。我猛地按下了暂停键。鼠标点击的声音在死寂的房间里异常清晰。
画面定格在那个瞬间。一个男人。身形瘦削,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旧风衣。风衣的样式,
尤其是那磨损的袖口轮廓,熟悉得如同刻在我自己的骨头上!帽子压得很低,
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个紧绷的下颌线条。他微微低着头,脚步迅捷而警觉,
像一只融入夜色的猫,迅速消失在走廊监控探头的边缘。风衣。我的风衣。
那件昨晚被我随手搭在客厅沙发上的风衣!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
骤然停止跳动,随即又以疯狂的频率擂鼓般撞击着胸腔。血液似乎瞬间冲上头顶,
又在下一秒冰冷地退去,留下眩晕和耳鸣。一股强烈的、冰冷的恶心感从胃里翻涌上来。
我死死盯着屏幕上那个模糊的身影,
那个穿着我衣服的、从曾丽所在的解剖室里走出来的身影。是我吗?怎么可能?
我昨晚明明……混乱的思绪如同被投入石子的泥潭,浑浊地翻腾。记忆试图回溯,
却像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布满尖刺的墙。昨夜……昨夜我确实进来了。我检查了曾丽的尸体,
确认了窒息征象,取了初步的检材……然后呢?然后发生了什么?
记忆从这里开始变得模糊、断裂,如同信号不良的电视画面,
充斥着刺眼的雪花点和令人不安的闪烁。我似乎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剧烈的眩晕,
像被无形的重锤击中后脑。眼前发黑,耳边是尖锐的鸣响……身体沉重地倒了下去?
不对……好像没有完全失去意识……那是一种诡异的半梦半醒状态……就在这时,
脑海深处猛地炸开一片刺目的白光!毫无预兆!仿佛有人强行撕开了我的颅骨,
塞入了一段燃烧的影像碎片!视野剧烈地摇晃、旋转,像是透过一个坏掉的万花筒。
画面极其不稳定,色彩失真,边缘扭曲。但无比清晰地,
我“看”到了——一只戴着薄橡胶手套的手!那是我惯用的、贴合度极高的乳胶检查手套!
这只手,正死死地扼住一段纤细的脖颈!青筋在手套下清晰地暴起,
指节因极度的用力而扭曲、发白。视线颤抖着向上移动,越过那只行凶的手,
我看到了被扼住的人的脸!曾丽!她的脸因极度的痛苦和窒息而扭曲变形,
嘴唇呈现出可怕的紫绀色,眼睛瞪得极大,瞳孔里倒映着上方行凶者的面容——那是我!
邓华淮!是我自己那张因暴戾和某种决绝的疯狂而同样扭曲的脸!她的嘴唇在艰难地翕动,
微弱的气流挤出几个破碎的音节:“来……不及……了……”嗡——!
脑海中的影像瞬间熄灭,如同烧断的灯丝。巨大的空白和尖锐的耳鸣接管了一切。
我踉跄着向后猛退一步,脊背重重撞在冰冷的金属器械柜上,发出“哐当”一声巨响!
金属柜门震动着,托盘里的手术刀、镊子、骨凿相互碰撞,发出清脆而混乱的叮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