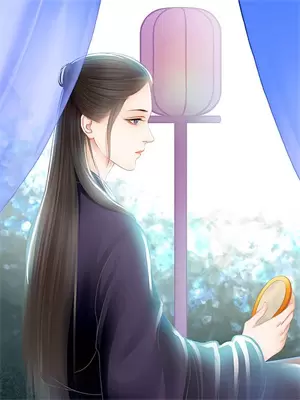和心理医生谈恋爱是什么体验?我的体验是,他想吃了我。字面意义上的那种。我有个秘密,
我的痛苦可以实体化。每次经历创伤,我都能把它从记忆里剥离出来,
变成一个灰色的小盒子。我把它们全都锁起来,眼不见心不烦。我的未婚夫顾云深,
就是一位心理医生。他知道我这个秘密后,非但没觉得我奇怪,反而将我拥入怀中,
说这是“最独特的自我保护天赋”。他说我是最纯净的珍宝,
因为我主动滤掉了世间所有的污秽。我信了。我以为我遇到了全世界最懂我的人,
直到他向我求婚成功。他捧着我的脸,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贪婪与饥渴。他说:“愿愿,
你的防御机制很完美,为我打造了一个最干净的‘食盆’。现在,开饭时间到了。
”1第1章 今儿个我又扔了个“糟心玩意儿”嘿,
今儿个我又把一个“糟心玩意儿”给扔喽。瞅瞅窗外,那雨跟不要钱似的可劲儿下,
雨点噼里啪啦地砸落地窗上,跟拿针扎黑咕隆咚的夜似的。我把脑瓜顶贴那冰凉的玻璃上,
手指头捏着张都泛黄的破照片。照片上,七八岁那阵儿的我,穿条贼不合身的公主裙,
猫在小学文艺汇演后台旮旯里。边上那几个打扮得人模狗样的丫头片子,正指着我嘎嘎乐,
都快笑抽抽了。她们当时说啥,我早忘球了,那些损人的话,早被我麻溜打包扔一边儿去了。
可那感觉,我死都忘不了,就跟光不溜秋让人塞冰柜里似的,冻得骨头都嘚瑟,
臊得我恨不得把自个儿缩成粒儿灰。我一闭眼,“呼”地猛吸口气。
手指头尖儿上冒起一丁点儿灰不溜秋的光,跟灰末儿似的,这光“嗖”一下就蹿开了,
“咔嚓”一下把那段膈应人的破事儿连根儿给薅出来。这么一整,给我脑袋都整晕乎了,
可没一会儿,就觉着心里头空落落的,倒也舒坦了。那灰光在我手心里头一聚,
末了儿变一跟巴掌差不多大的灰不溜秋木头盒儿。盒儿面上,还模模糊糊能瞅见个舞台影子。
“得嘞,被人孤立那滋味儿,拜拜了您嘞!” 嘿,我悄么声儿把话撂下,
心里头“咯噔”一下,这盒子“嗖”地一下就没影咯,
让我麻溜儿地塞到意识里头那老落灰的“记忆阁楼”里头去咧。把这事儿都弄完,
我“呼——”地长出了口气,觉着这满世界都亮堂得不行。正这当口儿,
手机“嗡嗡”直颤悠。瞅了眼,是发小陈默发过来的语音,背景那叫一个乱腾,
估摸是在KTV里头呢。就听他扯着嗓子喊:“愿愿,你可真不来参加同学聚会呐?
当年可劲儿踩你那几个货,如今都活得倍儿憋屈。就你,
都成了那贼火的绘本《情绪小怪兽》的作者,老有钱啦,还把顾云深那大男神给拿下咯。
你这会儿麻溜儿过去,往那儿一站,那不得把她们臊得没地儿钻,犯不着躲着呗!
”我乐呵儿一笑,慢悠悠地敲字回他:“我躲个啥呀,
我就觉着……不想再当那动不动就哭鼻子的小屁孩咧。”我可没跟他说,那天到底咋回事儿,
我早忘得没边儿啦。就那种“跟让人塞冰柜里似的”憋屈得要死的感觉,
这会儿正老老实实待在我记忆阁楼第三排,第七个盒子里头呢。我觉着自个儿都快美上天咯。
可代价就是,我那老些个过去,全跟空壳儿似的。转天一大早儿,我正睡得香呢,
“叮铃铃”一通电话给我薅醒咯。电话那头,我那助理声音都哆嗦成啥样了:“林老师!
完犊子啦!您那工作室……起火啦!”我这脑子“嗡”一下子,当时就懵圈儿,
啥念头都没了。那可老重要了,是我给咱市里最大那儿童情绪疗愈中心画的一整套绘本原稿,
我整整鼓捣仨月的心血啊,今儿个就得交活儿。我撒丫子疯了似地往工作室跑,到那儿一看,
警戒线外边围了一堆人。那老鼻子刺鼻的焦糊味儿直往我鼻子里钻,我瞅着那熏得黢黑的墙,
腿一软,差点没站住。消防员说,这火着得邪乎。监控瞅着昨儿夜里压根儿没人进也没人出,
火是打我平常使的那块绘图板那儿起的,头一遭儿寻思是里头线路短路了。
可我那绘图板上个月刚换的最新款啊。助理扶着我,
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嚎:“稿子……全给烧没啦,一张都没剩!”我这心口“咯噔”一下,
眼跟前直冒金星。正这节骨眼儿,有个消防员队长拎着个证物袋溜达过来,那表情老奇怪了。
“林小姐,咱在烧得最惨的那堆原稿纸里头,瞅见这玩意儿了。”他把那证物袋一举,
我滴个乖乖,里头躺了个灰不溜秋的木盒,跟我昨儿晚上封好的那个一模一样。
一堆让大火烧得都成灰的纸片子里头,就它屁事儿没有,稳稳当当立那儿。嘿!
我这小心脏“咯噔”一下,当时那心跳,“嗖”地就漏了一拍。咱可听好了啊,
这可老稀罕了,头一遭儿在现实里头,瞅见我那跟活物儿似的“记忆”,
跟真事儿似的就搁眼前儿立着。我强撑着,装得倍儿淡定,麻溜儿把那盒子捞回来。好家伙,
手指头刚一沾上那玩意儿,“刺溜”一下,一股子透心凉的寒气,“嗖”地就顺着皮儿,
直蹿我天灵盖儿,给我嘚瑟得。我跟那啥似的,死死把它攥手心里头,浑身跟筛糠似的,
抖得压根儿就停不下来。正哆嗦着呢,
就听一贼温柔、贼低沉的声儿在我耳朵边儿冒出来:“别怕,有我呢。”紧接着,
就觉着一物件儿“唰”地搭我肩膀上了,一股子淡淡的檀香味儿直往鼻子里头钻,我一瞅,
嘿,一件米白色的亚麻衬衫。还能有谁啊,可不就是顾云深嘛。我那未婚夫,
咱这地界儿谁不知道啊,“心屿”那老有名的心理诊所,就他捣鼓起来的。这哥们儿,
啥话都没多逼逼,伸手“啪”地就攥住我那跟冰块儿似的手,麻溜儿带我麻溜儿撤,
从那乱糟糟的地儿跑出来,一脚油门儿,“呜”地就干海边儿去了。
海边儿那风“呼呼”地吹,可算把那股子焦煳味儿给吹散了点儿。我那脑瓜子,
跟短路了似的,这会儿可算又能转起来了。顾云深塞给我一保温杯,里头温乎水。他那声儿,
跟大提琴拉出来似的,给我那紧绷巴的神经,“咵”地就给熨帖明白了。他瞅着我眼睛,
那眼神儿,老深老温柔了,跟能把人瞅透溜儿似的,张嘴就跟我说:“心里头那糟心事儿,
可别老憋着。但要是这玩意儿,都开始糟践你了,那就麻溜儿寻思寻思,换个地儿搁它。
”就这话一出来,我这眼泪,当时差点没“哗”一下就下来。嘿!他咋能……这么懂我咧?
满世界的人瞅见的我,那都是老阳光、贼开朗的主儿,就他,跟长了双透视眼似的,
一下就透过我那倍儿完美的模样,瞅见我心里头那空落落的荒滩子了。就那会儿,
我麻溜儿做了个决定。我“唰”地一下拽过他那热乎的手心儿,拿手指头,在他手心里头,
一笔一划地画了道贼拉复杂的符纹,也就我知道这玩意儿啥意思。
这可就是打开我那“记忆阁楼”的独一份儿钥匙。我藏得最深的那秘密,
头一遭儿给第二个人敞开了门儿。顾云深直勾勾盯着我眼睛,觉着手指头底下那道儿,
脸上“唰”地就挂了个老温柔的笑。“等咱俩结婚那天,”他轻手轻脚攥住我的手,
跟攥着天底下顶值钱的宝贝似的,“让我瞅瞅你的里里外外,成不?
”我瞅着他那老深情的眼神儿,脑袋跟捣蒜似的“哐哐”点头。就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我梦着自个儿又跑那封了老久的记忆阁楼去了。那阁楼上死静死静的,瞅着瘆得慌,
一排一排架子上,全是大盒小盒,堆得那叫一个密。
失恋的、让人给耍了的、考试考砸的、当大伙面儿让人给埋汰的……啥糟心事儿都有,
我全给整成不会吱声儿的标本搁里头了。可今儿个,咋觉着哪儿不对劲儿呢。嘿!
我瞅见了哈,在那阁楼老深老深的地儿,有个老大、老古董的黑盒子,
上头刻着那血呼啦的纹路,正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地抖悠呢。那可不咋的,打我七岁那年起,
我可就记着,眼睁睁瞅见我妈出车祸没了,这事儿就跟钉子似的钉我心里头。这黑盒子,
那是我头一回得着的盒子,也是我压根儿就没敢扒拉的、老深老深的一块儿心病。
正我这儿心里头七上八下,跟揣了只兔子似的,就听那阁楼的木头楼梯口,
传来“噔噔噔”一阵脚步声,一听就不是自个儿的,那步子老稳当了。我“嗖”一下回头。
嘿哟,顾云深那小子,逆着光,跟个幽灵似的出现在楼梯口。瞅瞅他,穿一身板正的西装,
脸上还挂着那贼熟悉的,跟抹了蜜似的笑。就瞧见他手里头,明晃晃攥着把钥匙,
跟我那把一模一样,上头全是些花里胡哨的符纹。他贼眉鼠眼地扫了一圈满屋子的盒子,
又拿眼溜了我一下,末了儿,眼神儿定那正抖的带血纹的黑盒子上了。那眼神儿,我瞅着,
啧啧,那股子馋得慌跟美滋儿滋儿的劲儿,我压根儿就没瞅见过。
他不紧不慢地朝我溜达过来,那声儿软得跟小情侣在一块儿腻歪似的。“哟呵,
敢情你连这玩意儿都留着……”“可真是个听话宝儿。”我“嗷”一嗓子从梦里头吓醒,
后背跟冰碴子似的,睡衣早让冷汗给洇透咯。我跟个破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直喘气儿,
一眨巴眼,下意识扭头瞅那床头柜。就瞅见从火里头抢出来的那灰不溜秋的木盒子,
稳当当搁那儿呢。嘿,瞧见没,就那么一丁点儿贼拉微弱的红乎雾气,正从那盒子缝儿里,
慢悠悠地往外渗呢。这时候,手机屏幕“唰”地亮了,是顾云深发过来的信儿。“愿愿,
醒没?这婚礼操持起来老麻烦了,我寻思着,咱先整个就咱俩的小仪式呗。
”“就搁婚礼前俩礼拜,上我城郊那老宅子去。”“那儿静悄悄的,压根儿没旁人能打扰咱。
”我瞅着那字儿,这心呐,跟让只没影的手给揪住似的,
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往老冷老冷的海底沉。就那老宅子,他早先还说呢,
里头装着他一肚子的秘密。我那会儿哪能知道啊,合着他早把那地儿,
给我当成坟圈子预备好了。2第2章 他拉开我抽屉那会,眼珠子直冒绿光嘿,
离办婚礼还有俩礼拜呢,顾云深开着他那辆贼拉帅的黑宾利,
麻溜地带我往城郊那老宅子去了。他还大言不惭地说,要给我整一场就咱俩的私密仪式。
咱就说,那车“嗖”一下就跑出城了,把那热闹劲儿全甩后头,路边瞅着那景儿,
越来越荒得没边儿。末了儿,“嘎吱”一下,停一爬满爬山虎的英国老房子跟前儿。
那铁大门锈得都没样儿了,一推“吱呀吱呀”直叫唤,跟快咽气儿的老头儿似的。
顾云深拽着我手,嬉皮笑脸地说:“这儿我打小长大的地儿,是旧了吧唧的,
你可别挑刺儿啊。”他笑是笑了,可我咋瞅着,那笑让那宅子的黑影给罩得,
压根儿看不清啥样儿。我一抬脚跨进那屋,心里“咯噔”一下,直犯怵。再瞅瞅那客厅,
装得倒是古里古气挺讲究,可咋瞅咋觉着邪性。最扎眼的,就壁炉上头挂那老大一面破镜子。
那镜子椭圆儿的,框子是啥老黑木头雕的,上头刻那玩意儿,曲里拐弯儿,密麻麻一片,
跟鬼画符似的。我瞅见那玩意儿,当时气儿都倒抽一口,差点没背过去。为啥呢?嘿,
那鬼画符跟我脑瓜里头那“记忆阁楼”门环上的图案,一丁点儿差头儿都没!
“瞅着老稀罕了,对吧?”顾云深顺着我眼神儿一瞧,那语气里带了老些念想,
“咱家族传下来的老物件儿,听说能照出人心底那点儿事儿。”他溜达上前,
伸出那大长手指头,随随便便就把镜子面上那层薄灰给抹拉下去了。
就瞅见他手指头刚碰上那冰拔凉的镜面儿,我脑瓜儿里“咔哒”一下,听得真真儿的。
这声儿,瞅着跟打那老远贼空荡的阁楼旮旯传出来似的,就跟啥生锈的锁头,
让把没影的钥匙给捅开了似的。我一哆嗦,下意识攥紧了手心儿,
打脚底心“嗖”一下蹿上来一股凉气儿,直顶脑瓜门儿。“咋咧,愿愿?脸白得跟纸似的!
”他一回头,可着劲儿瞅我,眼神儿里全是担心。我赶紧摇头,硬挤出个笑:“嗐,
没啥事儿,许是低血糖犯了。”他也没刨根问底儿,麻溜儿给我沏了杯热茶,
完了领我到沙发那儿坐下。“婚礼请的人儿那名单,我都让晚晴给弄好咧,她下午就送过来。
你瞅瞅还有没啥要添的不。”苏晚晴,就顾云深那诊所当助理那女的,
听说早先还在他那儿瞧过病。我见过她好几回,成天儿悄没声儿地猫顾云深屁股后头,
跟个没脾气的影子似的。下午三点,门铃“叮咚”一响,准得不能再准。苏晚晴在门口戳着,
塞给我一摞老厚的材料。“林小姐,这、这是……名单。”她那声儿跟蚊子哼哼似的,
眼神儿直乱飘,压根儿不敢跟我眼神对上。她手哆嗦得都没边儿了,
那几张破纸都快拿不住喽。我一不留神儿,眼神儿扫到她手腕上,
眼珠子“嗖”一下就瞪大了。就瞧她那白花花手腕里头,有一圈儿焦黑焦黑的印子,
瞅着跟拿滚烫的烙铁烫出来的五根手指头印子似的,跟个大怪物似的趴在她皮肤上。
她估摸着觉摸着我瞅她呢,跟遭雷劈了似的,“唰”一下把手抽回去,麻溜儿地把长袖一拉,
把那瘆人的印子给挡住了。“你……”我刚想张嘴问问咋回事儿。可她倒好,
跟见着啥吓破胆儿的玩意儿似的,
突然就自个儿嘟囔开了:“顾医生说……那些糟心巴拉的坏情绪,隔三岔五就得清一清,
要不灵魂都得烂喽……对喽,得给收拾干净……”“清理?啥玩意儿叫清理啊?
”我紧着追问。苏晚晴那眼神儿,散得没边儿,在我脸上就停了那么一秒,
瞅着跟那没底儿的枯井似的,空落落吓人巴拉的。
“我压根儿记不起那些糟心事儿喽……啥都记不起来喽……”她迷迷瞪瞪地直摇头,
嘴皮子直嘚瑟,“可咋滴……我咋还觉着饿得不行……饿得要命嘞……”话都还没说完,
她瞅着是一点儿劲儿都没啦,一转身,跌跌撞撞撒丫子就跑,跟屁股后头有索命鬼撵她似的。
给我搁原地都瞅傻愣了,手脚冰凉透心凉。嘿!咋不记着那老遭罪的事儿,
反倒肚子咕噜咕噜叫唤,觉着饿啦?就这天黑了,我逮个由头,说自个儿一路车马劳顿的,
麻溜回屋,“哐当”一下躺床上。我装得跟死猪似睡熟了,可耳朵跟那雷达似的,
支棱得倍儿直,就盼着听门外有啥动静。眼瞅着到半夜十二点,就听着那“沙沙”的脚步声,
轻得跟猫似的。嘿,就瞅见顾云深从他那屋溜达出来,瞅那方向,直奔书房去咧。
我跟个贼似的,悄没声儿地就跟过去,“嗖”一下把自个儿藏门缝边那黑影里头,
顺着那窄不拉几的门缝,抻着脖子往里瞧。书房里黑灯瞎火的,啥亮堂玩意儿都没,
就那破古镜子,让月光一照,跟鬼火似,幽幽地冒冷光。就瞅见顾云深自个儿杵镜子跟前儿。
他从兜儿里掏出个透亮儿的小塑料袋,我一瞧,好家伙,里头竟装着一绺头发。
我能不认得嘛,那可不就是苏晚晴那头发嘛。
他“啪”一下把那绺头发扔古镜子跟前儿那香炉里,火苗“刺啦”一下“噌”老高,
把他半拉脸照得一会儿亮一会儿暗的。他“啪嗒”一下闭上眼,俩手跟变戏法儿似,
比划出个老邪乎的手势,嘴里还叽里咕噜念叨些老掉牙的词儿。“归藏·引浊·奉飨。
”他那声儿,跟破锣似,又低又哑,跟老辈子搞啥祭神拜鬼的玩意儿念的词儿似的。
他这话音儿刚落,就瞅那镜子面儿上,“咕噜咕噜”冒起一遭遭墨绿的波纹,
跟往湖里扔块石头溅起的水花儿似。紧跟着,就瞅那镜子里头,
乌央乌央冒出来老多跟灰不溜秋小盒子似的虚影,跟那小尘埃似。嘿!你瞅那堆盒子,
跟疯了似的又挣又扎,哐当哐当直撞,末了一个接一个“啪叽”就崩碎咧,
全化成老浓稠、一眼就能瞅见的黑咕隆咚的雾。顾云深脑袋一扬,瞅着那镜子,
“呼”地猛吸了一大口气。那黑雾气跟抢啥宝贝似的,“呼呼”地从镜子里往外冒,
“嗖”一下就钻进他鼻子里去咧。就瞅他那喉结,上上下下直动弹,那脸上的表情,
跟那啥整到高潮似的,老陶醉、老得劲儿了。给我吓得,嘴都快让我捂烂乎了,
才没扯着嗓子嗷嗷叫唤出来。害怕得我哟,就跟有老多冰凉的手掐我心口窝似的,
憋得我都快上不来气儿咧。我浑身直嘚瑟,一步一挪地往后退,
退回屋“哐当”一下把门反锁上,整个人“噗通”一下瘫地上了。
哎呀我这才反应过来咋回事儿。我麻溜儿闭上眼,使足了老劲儿,
一头扎进自个儿脑瓜里那旮沓。嘿,瞅见那老熟的“记忆阁楼”啦。可这回头儿,
阁楼里可不像老早先儿死巴登登的。空气里头,飘了老些稀了咣当的灰,
就那盒子碎完剩的玩意儿。我撒丫子就往那老熟的架子那儿跑,心都快从嗓子眼儿蹦出来咧。
可不咋的——原先摆着“让上司在职场上往死里欺负”那玩意儿的架子,
秃噜光净儿的啥都没咧。原先搁“让初恋对象给绿了”那盒子的地儿,也啥都没剩。嘿,
就连那个代表“我爹再婚那天,我自个儿孤孤单单坐那空落落家里”的盒子,都没影啦。
可倒好,它们全给人打开喽。里头藏着的那些憋屈、难受、气不打一处来的玩意儿,全没啦。
再瞅瞅我这心口窝子,跟让人硬生生剜下去三大块肉似的,空捞捞地直犯疼,
那股子没着没落的劲儿,差点给我恶心吐喽。我还觉着那是保险得不能再保险的地儿呢,
自个儿寻思着那是天底下最安全的避风港,闹了半天,
早八百年就给那些馋得直吧嗒嘴的家伙敞开大门啦。
我千小心万小心扒拉出来、藏好的那些糟心事儿,早成人家嘴里的肉啦。转天一大早,
房门稀里哗啦让人轻轻推开。顾云深端着一份倍儿精致的早饭进来了,
脸上那笑还跟往常似的,跟个大暖男似的,昨儿夜里那跟吞了一肚子黑玩意儿的怪物,
瞅着都跟我做梦瞎寻思的似的。“愿愿,昨儿晚上睡得咋样啊?
”他把那餐盘往床头柜上一撂,一屁股坐到我床边。我跟个木头似的直勾勾瞅着他,
憋半天一个字儿都吐不出来。他跟没瞅见我不对劲似的,伸手过来,轻手轻脚摩挲我头发,
可那眼神儿里,“唰”地闪过一道绿汪汪的光,跟那野牲口似的,我压根儿就没瞅见过。
“你知道不,你在我瞅见的里头,那就是保存得最齐整的‘宝贝疙瘩’。
”他那声儿轻得跟蚊子叫似的,可听我耳朵里,
跟拿淬了毒的冰锥子“哐当”一下扎我耳朵眼儿里似的。嘿!二十多年啦,
整整三百一十二个老带劲的负面记忆单元呐……林愿,你妥妥就是给我量身造的大花园儿!
他呼一下俯下身,鼻尖儿都快贴我脸上喽,那声儿老低沉了,听着就让人直起鸡皮疙瘩,
透着股子老痴迷的味儿。“等咱俩把那婚一结,我高低得把你那颗最后嘞核心种子给摘喽。
”他那眼神儿,跟能透视似的,“唰”一下就透过我这皮肉,直勾勾瞅我灵魂最里头去咧。
“你妈死那天那全套记忆,里头那老透顶的害怕跟憋屈,指定……老甜溜儿了。”得嘞,
我这世界,就这会儿“哐当”一下全塌稀碎。合着他压根儿就不是来救我的大英雄,
他就是一养我的主儿。瞅瞅我自个儿,可不就是他巴巴儿养了二十多年,
就等熟了好下嘴的一果子嘛。我瞅着跟前儿他那张,长得是俊巴儿俊,可跟那恶魔似的脸,
浑身血都给冻住咧。可瞅着他那副志在必得的死出,我倒好,吭哧瘪肚儿还硬挤出个笑。
“云深,”我张嘴,嘿,那声儿愣是一点儿没哆嗦,“办那婚礼老麻烦了,
我寻思……就搁这儿猫着,自个儿静静,好好捯饬捯饬我那嫁妆,
也顺顺我这一肚子糟心巴拉的事儿。3第3章 我又把那老遭罪的破盒子,
给塞自个儿心里头咯嘿,就瞅那顾云深,眼睛里头那得意都快冒出来啦,跟要溢出来似的。
他一哈腰,在我脑门上“吧唧”亲了一口,那嘴凉飕飕的,跟拿自个儿东西做记号似的。
“那可不咋的,我宝贝儿愿愿。你那嫁妆,是得好好拾掇拾掇。我等你哈。
”说完他麻溜儿转身就走,步子迈得那叫一个轻快,跟猎人收网前那老有谱儿似的。
他还美呢,觉着我正巴巴儿给他备那老丰盛的大餐呢。可他哪儿能知道啊,
我正悄摸儿磨那报仇的刀呢。得嘞,我让人给安排到那老宅二楼一偏厅住下了,
还整了个好听名儿,叫啥“新娘的祈祷室”。瞅那窗外,花园里全是些枯了吧唧的玩意儿。
屋里头也没啥玩意儿,就摆了个老大的梳妆台,那镜子还给拿老厚一白布给蒙上了。
我才不稀得碰那些啥嫁妆呢,瞅着那些老好看的珠宝、衣裳啥的,在我眼里头,
跟给死人上供的花活儿没啥两样。我心里头就惦记一件事儿,找这宅子藏着的那老些个秘密。
我就瞎编个瞎话,说找能配婚纱的老物件儿,逮着守宅子那周叔,打听那储藏室搁哪儿。
周叔那俩眼睛,浑得跟啥似的,里头“唰”一下闪过害怕跟不忍,嘴唇子都哆嗦起来了。
末了儿,就拿那手指头老粗的手指头,冲那通地下室那门指了指。“小姐……有些玩意儿,
瞅见了可没好,别去看嘞。”他扯着个破锣嗓子,跟说啥见不得人的事儿似的。嘿,
我就冲他点了点头,可心里头那叫一个明镜儿似的,铁定那儿藏着我要找的答案。那地下室,
老阴冷潮湿啦,一股子尘土味儿跟烂木头味儿,熏得人直犯恶心。我借着手机那丁点儿亮光,
在那堆老厚灰的破烂玩意儿里头扒拉。可算让我摸着一本老厚的书,
外皮是黑不溜秋的皮子包着。瞅那封面儿,连个书名都没有,
就仨烫金的老古篆字儿——《顾氏家仪》。我“噗”地一吹那上头的灰,
“唰”地就把那黄巴巴、软塌塌跟纸糊似的书页给翻开了。我嘞个去,
里头记的压根儿不是啥家族规矩,净是些邪了吧唧的祖传邪术。
就瞅见上头写着:“赶上癸亥那年,
当家的得把‘归心客’迎家里头……”我这眼珠子一下就跟粘那“归心客”仨字儿上似的,
死活挪不动道儿。再一瞧书页上说,这归心客,那就是打娘胎里出来就是个“大罐子”,
啥世上的七情六欲都能往自个儿心里头装,是喂那“虚相”的顶好的主儿。
还写着“……拿九阴身子的人儿献祭一百天,把那‘虚相’给招来,就能长生不老喽。
”再往后翻,书末还画着一老逼真的人儿。画里那老爷们儿手里举着面老铜镜,
仰着脖儿可劲儿吞从镜子里冒出来的黑玩意儿。再一瞅他脑瓜门儿正中间儿,好家伙,
明晃晃长着一细长条、邪性巴拉的竖眼珠子。嘿!你瞅那张脸,除了脑门上那竖瞳,好家伙,
跟顾云深书房挂的那张他年轻时候照片,简直一摸一样!这头正惊着呐,千里外那城市里,
我发小陈默跟个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急得直溜达。他啥人啊?黑客呗!
也就他隐隐约约觉着顾云深这人不地道。我失联前,给他发了条信儿:“小心镜子。
”这会儿,他可倒好,胆儿肥了,硬闯顾云深那叫“心屿”的心理诊所,
咔咔撬开档案室的门。在贴“S”级标签那保密档案柜里,扒拉出苏晚晴的病历。
病历上“重度抑郁”那诊断,瞅着老吓人了。再看顾云深给的那治疗方案,
就一行字:“情绪剥离疗法”。病程记录上写着,治完了,苏晚晴那情绪稳得离谱,
一点儿糟心的样儿都没了,可跟着来个邪乎事儿,饿起来没个够。
她一天能造进去老多高热量的吃食,体重反倒跟坐滑梯似的,蹭蹭往下掉。
陈默翻到最后一页,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就顾云深那亲笔写的备注,字儿倒是好看,
可瞅着瘆得慌:“第7号宿体能量不够,没啥活力了,瞅着也没啥瞧头,撤了吧。” 嘿!
啥?宿体?7号?陈默那家伙,吓得手脚都冰凉透顶了,麻溜儿地就拨我电话。
电话倒是通了,可接起来的是个老帮子,声音又老又哑。哟呵,是周叔。周叔那声儿,
透着老鼻子绝望了,“别打啦,白费劲儿!现下这顾先生……压根儿就不是个人啦!”说完,
“啪”一下就把电话给挂喽。再瞅老宅外边儿,嘿,那暴风雨可算来喽。风嗷嗷地刮,
雨点儿跟豆粒儿似的,“噼里啪啦”可劲儿往玻璃上砸。“咔嚓”一道白花花的闪电,
“唰”一下把天给劈开,这老宅“嗡”一下子,电没啦,黑咕隆咚,一点儿动静都没,
死静死静的。就这会儿!我“啪”一下把手里那破古籍扔一边儿,
撒丫子就往自个儿意识里头猛冲,跟疯了似的。
我得赶在顾云深对我来那啥最后“采摘”之前,把自个儿那玩意儿全抢回来!
可等我跟头把式跑到那熟得不能再熟的“记忆阁楼”跟前儿,瞅见那门儿,
我这心“咯噔”一下,凉透喽。原先半掩着的门儿,
这会儿叫一道道绿了吧唧的符文给死死锁住,一点儿缝儿都没。嘿,就那符文,
跟那古镜框子上的一模一样!我使足了吃奶的劲儿,又推又撞,那门儿跟长死了似的,
屁都不带动一下。正折腾呢,我脑袋里头“哐当”冒出来个贼拉冰凉的声儿:想开门?行!
拿一段新的、老鼻子疼的事儿献祭,门儿兴许能开!啥?全新的痛苦?
我那些老鼻子深的痛苦,不都早给封在里头了嘛?眼瞅着到节骨眼儿上,
顾云深昨儿夜里说的那话,“唰”一下跟道闪电似的,劈我脑袋里了。
他当时说:“你妈死那天的全乎记忆,那老鼻子恐惧跟绝望了,指定……老甜了。”嘿,
他咋能知道得这么门儿清啊?就那害怕劲儿、那憋屈样儿,他知道的比我自个儿都细溜!
一个我都给压箱底儿快二十年,连自个儿都觉着是瞎琢磨的念想,“呼”一下就冒出来了。
保不齐,那压根儿就不是啥意外。我“嗷”一嗓子,照着舌尖就是一口,
那铁锈味儿的老剧痛,还有血那股子甜腥味,“轰”一下在嘴里炸开了。
我就拿这股子疼当钥匙,硬给记忆最里头那道封条给撕巴开了。想当年我七岁那阵儿,
赶上一雷雨天儿。我妈开车,要带我去参加一贼重要的钢琴比赛。走到半道儿,“呜”一下,
一老大个大货车,横冲直撞逆着就过来了,那车灯贼亮,晃得我压根儿睁不开眼。
眼瞅着就要撞上了。我透过那糊满雨水的车窗,瞅得倍儿清楚,道边黑影里头,
站着一穿黑大氅的老爷们儿。他手里头,正举着一面老古董镜子,
上头刻着贼拉复杂的花活儿。嘿!那镜子正对着咱这车呢。
风呼一下子就把他那兜帽给吹起来喽,露出来一张脸,瞅着挺年轻,可一点儿活气儿都没。
哟呵,这不顾云深嘛!闹了半天,就是他拿那破镜子,整出这场车祸的!“啊——!
”我扯着嗓子嗷一嗓子,那动静,老撕心裂肺了。嘿,这哪是啥回忆啊,
分明就是让人给藏起来的真相!眼泪跟嘴角那血都掺一块儿了,稀里哗啦往下淌。
这心里头刚冒出来的憋屈、恨意,老上头了,能把人魂儿都给碾巴碎咯,
“腾”一下子就化成一股邪火儿。我铆足了浑身的劲儿,
“哐当”一下就往那阁楼大门上撞过去!那门上的符文还直闪呢。“轰——!
”门“哗啦”一下就开了。我跟道闪电似的,
“嗖”一下子就扑那阁楼正中间那黑盒子跟前儿去了。那盒子上老些锁链捆着,
还画着血了呼啦的纹路。这可不就是装着我妈咋没了那事儿的盒子嘛,我遭那老鼻子罪,
全打这儿来的。顾云深那孙子还老稀罕这玩意儿,管它叫啥老甜美的“核心种子”。“别动!
”身后“嗷”一嗓子,顾云深那孙子急眼了,可算觉着不对劲儿,一脚把门踹开跑进来了。
瞅瞅他那德行,一点儿人模狗样儿都没了,脸都扭曲得跟恶鬼似的,
跟吃了枪药似的嗷嗷叫唤。哼,晚喽!嘿,就瞅见他猛扑过来那刹那,
我麻溜儿地双手一抄起那盒子,眼皮儿都没眨巴一下,当着他面儿,
“嘎吱”一下狠狠给捏碎咯!我把那跟墨汁儿似的老浓稠的玩意儿,
那可全是跟我妈死有关的憋屈玩意儿——啥伤心呐、火大呐、憋屈得慌呐,
还有那爱跟没了的滋味儿——“咕噜”一下全给吞自个儿肚子里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工夫,
我浑身跟筛糠似的抖得那叫一个厉害,感觉自个儿跟扔炼人炉里头似的,
骨头缝儿里、神经末梢儿,全跟叫唤似的。早先儿落下的伤那疼劲儿“嗖”一下又冒出来,
疼得我都快腿一软跪地上了,可我硬咬牙撑着,慢悠儿地把脊梁骨给挺得倍儿直,
直勾勾盯着一步一步往上凑的顾云深。我“咝溜”一下把嘴角那血舔了,
冲他“嘿”一声乐了。“哟呵,你说这些玩意儿是垃圾?”“可就靠这些,
咱才活成个人样儿!”“瞅瞅你……也就配捡那剩玩意儿,活成一没魂儿的影子!
”这话一撂下,我这俩眼珠子里头“腾”一下冒出来的,可不再是那没边儿没沿儿的乐呵,
也不是让人抢了东西后的那股子愣神儿劲儿,那是一股子热乎拉乎、实实在在,
又带爱又带恨的大火苗子!顾云深那脸上的笑模样,头一遭儿跟让胶水儿粘住似的,
僵那儿了。就瞅他那帅得没边儿的脸,眼角那儿“咵嚓”一道小缝儿,跟鬼似的,
悄没声儿就爬开了。4第4章 我把自个儿那记忆阁楼给烧咯那道裂纹,
瞅着就跟在那贼啦完美的瓷器上划的最后一笔似的,明摆着一场咋都挽回不了的稀碎要来了。
顾云深一不留神就抬手,寻思摸摸自个儿眼角那不对劲的地儿,可还没等他把手抬起来呢,
“咔”一下就跟被定住了似的。他脸上那暴脾气和凶巴巴的样儿,“唰”地一下就没了,
换上了一脸他娘的从没见过的懵圈跟害怕。为啥呢?就因为我抢回来的,
压根儿不只是一段破记忆。那是二十年憋屈老久、憋得都快冒火星子、浓缩得不能再浓缩的,
跟岩浆似的滚烫的老憋屈啦。我妈快咽气那会儿,死死攥着我的那手,
咋一点一点从热乎变得冰凉,我可都记起来了。那大暴雨夜,
那刹车声跟金属嘎巴嘎巴扭曲的动静,跟拿大锥子扎我耳朵似的,老清楚了。殡仪馆里头,
那块冰凉的白布底下,那鼓起来的啥玩意儿,硬邦邦的,死倔死倔的。
那些我早都当垃圾扔一边儿的真事儿,这会儿跟打雷似的,“轰隆隆”全杀回来咯。
“哎哟我去——!”我压根儿撑不住了,
“扑通”一下俩膝盖狠狠砸那记忆阁楼冰凉的地板上,手指甲都快抠进木板缝儿里去了,
嗓子眼儿里憋老久的动静,压根儿不像是人嚎出来的。
我觉着自个儿那魂儿都让人活生生给撕巴烂了,完了拿烙铁翻来覆去地烙。嘿!
咱每根神经都跟疯了似的嗷嗷叫唤,浑身那肉啊血啊,都跟筛糠似的直哆嗦。
再瞅瞅站门口那顾云深,脸上那股子美滋儿美滋儿的劲儿都还没全消呢,
可胸脯子猛不丁一紧巴,就跟咱俩之间有根瞅不见的线,让我跟个愣头青似的,
“咔嚓”一下给扯断喽。他脑袋一耷拉,瞅自个儿手背上,眼珠子都快瞪出来喽。
就瞧那手背上,眼见着“唰唰”地冒出来一片跟蜘蛛网似的灰道子,
跟那旱得都裂了缝儿的河床似的。嘿,这啥玩意儿?这是“养料”倒着往回跑呢。可不咋的,
就是我,正从他身上,把自个儿那玩意儿给抢回来呢。“别介……”他在那儿嘟嘟囔囔,
头一遭儿露出来那副跟挨了逮的猎物似的慌里慌张样儿,
“这可都是我的……”我才懒得搭理他。疼得我“嗷”一嗓子,这才回过神儿来,
瞅见自个儿正跟那老宅偏厅冰凉的地儿上瘫着,浑身早让冷汗给洇透喽,嘴角那嘎达血嘎巴,
齁咸齁腥的。再瞅瞅窗外,雨跟瓢泼似的,可劲儿往下倒。咱啥时候怕过?眼泪儿没掉一滴,
腿肚子也没打哆嗦。一睁眼,头一桩事儿,就麻溜儿伸出俩抖得跟筛子似的手,
从行李箱最旮旯的夹层里头,扒拉出一本边儿都磨秃噜皮的破速写本。这玩意儿,
可是打小儿画的,压根儿没搁电脑里存,也没扔喽。里头画的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