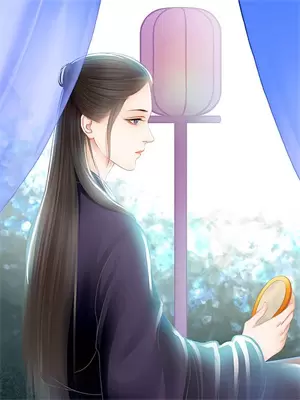入住当晚,小雅在槐树下发现一个刻着我们所有人名字的木牌。 第二天清晨,
林晓晓的床头出现了一缕与槐树上挂着的祈福袋相同的红绳。 我们试图逃离,
却总在绕了一圈后回到旅馆门口。 老板笑着说:“槐树喜欢你们,它想把你们永远留下来。
” 当失踪的小雅再次出现时,她已经成了槐树的新娘,头发里长出了细嫩的槐树枝。
“下一个就是我。”她微笑着指向我,而我手中的木牌上,名字正一个个消失。
雨下得正大的时候,那栋老旧的旅馆终于从盘山公路尽头浓得化不开的暮色里,
影影绰绰地显露出来。灰扑扑的三层小楼,墙皮剥落得厉害,露出里面深浅不一的砖石痕迹,
像一块块丑陋的疮疤。它孤零零地杵在山路的急弯旁,
背后是黑压压的、仿佛没有尽头的山林。最扎眼的,是院门口那棵巨大的槐树,
枝叶虬结伸展,浓密得几乎遮住了半边天空,在越来越暗的天光里,
投下一片沉重得令人喘不过气的阴影。“就是这儿了?”林晓晓把脸贴在冰凉的车窗上,
声音带着点抱怨的鼻音,“看着……怎么跟宣传图片上不太一样啊。”开车的李悦没吭声,
只是用力握了握方向盘,指节有些发白。
她费了好大劲才把这辆租来的小破车停在旅馆那歪歪扭扭的木质招牌旁——“槐下旅馆”,
四个字的油漆都剥落了不少,显得有气无力。我推开车门,
一股混合着泥土腥味和某种若有若无的、腐败甜腻气息的风立刻灌了进来,
让人忍不住打了个寒噤。小雅最后一个下车,她一直很安静,这会儿却微微仰着头,
目光越过旅馆低矮的院墙,直直地落在那棵巨大的槐树上,眼神里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这树……真大。”她轻声说,声音几乎被淅淅沥沥的雨声盖过。
旅馆内部比外面看起来更加破败。前台只有一个穿着灰布褂子的老头,低着头在算账,
算盘珠子拨得噼啪作响,对我们的到来毫无反应。灯光昏黄,勉强照亮着不大的空间,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年深日久的灰尘和木头霉变的味道。墙壁上糊着早已发黄变脆的报纸,
角落里堆着些看不清模样的杂物,蛛网在房梁角落肆无忌惮地牵连着。
老头给我们开了两间房,二楼的相邻间。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发出令人牙酸的“嘎吱”声,
在寂静的旅馆里显得格外刺耳。走廊又深又长,两侧的房间门都紧闭着,漆成暗红色,
像凝固的血。我们的房间在走廊尽头。房间不大,陈设简单到近乎简陋。两张硬板床,
一张木头桌子,桌面上甚至能看到油腻的污渍。窗户正对着院门口那棵大槐树,
繁茂的枝叶几乎要贴到玻璃上。雨点敲打着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那声音无孔不入,
听得人心烦意乱。“将就一晚吧,明天一早就走。”李悦把行李扔在地上,
试图让语气轻松些,但效果不佳。晚饭是老头端来的,简单的素菜和米饭,味道寡淡。
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没什么胃口,气氛有些沉闷。只有小雅,吃得心不在焉,
眼神时不时地飘向窗外那棵在风雨中摇曳的巨树。“我出去透透气。”她放下筷子,忽然说。
“这么晚了,还下着雨……”林晓晓想阻止。“就在院子里,很快回来。”小雅已经站起身,
径直走了出去。我们三个留在房间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内容无非是课程、实习,
还有对这次匆忙旅行的些许后悔。窗外的雨声似乎更急了,
槐树的影子在窗帘上投下张牙舞爪的图案。过了大概二十多分钟,小雅还没回来。
林晓晓有些坐不住了:“她怎么去那么久?”李悦站起身:“我去看看。”她刚拉开门,
小雅就站在门口,脸色有些异样的苍白,头发和肩膀都被雨水打湿了,但她似乎毫无所觉。
她摊开手掌,掌心躺着一块深褐色的木牌,边缘粗糙,像是随手从什么木头上掰下来的,
表面被摩挲得有些光滑。“在树下捡到的。”小雅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我们凑过去看。木牌不大,上面没有图案,只有几道歪歪扭扭的刻痕。
就着房间里昏暗的灯光,我们辨认出了那是什么——四个名字。李悦、林晓晓、苏婷、小雅。
正是我们四个。一股寒意瞬间从脊椎骨窜了上来,头皮阵阵发麻。“谁……谁的恶作剧吧?
”林晓晓强笑着说,声音却抖得厉害。李悦一把抓过木牌,翻来覆去地看,
脸色也越来越难看:“这痕迹很新,像是刚刻上去没多久。”我苏婷接过木牌,
指尖触碰到那刻痕,一种难以言喻的冰冷顺着指尖蔓延开来。木牌的材质,
和窗外那棵老槐树,几乎一模一样。“会不会是旅馆老板?”林晓晓猜测。“他?
他看起来根本懒得搭理我们。”李悦否定道,眉头紧锁,“而且,他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字?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窗外的雨声和槐树的摇曳声,仿佛成了这寂静夜里唯一的背景音,
衬得房间里的空气愈发凝滞。那块写着我们名字的木牌,像一块冰,
沉甸甸地压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头。那一晚睡得极不安稳。床板硬得硌人,
房间里总有若有若无的霉味往鼻子里钻。窗外的风穿过槐树叶的缝隙,发出呜呜咽咽的怪声,
时而像远处女人的哭泣,时而又像近在耳边的窃窃私语。我做了许多支离破碎的噩梦,
梦里总能看到那棵槐树,它的枝条像无数只干枯的手臂,在空中扭曲、挥舞。第二天清晨,
我是被林晓晓一声短促而尖利的惊叫吓醒的。“啊——!”她的声音充满了恐惧,
几乎变了调。我和李悦同时从床上弹起来,只见林晓晓蜷缩在她那张床的床头,
手指颤抖地指着枕头边。那里,安静地躺着一小缕红色的丝线,编结成简单的绳结样式,
颜色鲜艳得刺眼。几乎不用思考,我们同时扑到窗边,看向院中那棵槐树。繁茂的枝叶间,
果然悬挂着许多同样颜色的祈福袋,下面垂着长长的、一模一样的红色流苏。
在清晨灰白的天光下,那些红色的小点,像一只只窥视的眼睛。林晓晓枕头边的那一缕红绳,
与树上的,分明是同一种!“谁干的?谁放进来的?!”林晓晓的声音带上了哭腔,
脸色惨白。她昨晚睡得很沉,根本没有任何感觉。李悦一把抓过那缕红绳,
触手竟有一种阴冷的滑腻感。她猛地转身,拉开房门。走廊里空无一人,
只有尽头那扇窗户透进微弱的光。她冲到隔壁我们的房间,推开门,里面一切如常,
小雅还睡在床上,似乎没有被吵醒。恐惧像冰冷的藤蔓,瞬间缠紧了心脏。这不是恶作剧。
那块木牌,这缕红绳,都透着一种无法理解的邪门。“这地方不能待了!”李悦当机立断,
声音斩钉截铁,“收拾东西,马上走!”没有人有异议。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胡乱将行李塞进背包,甚至顾不上洗漱。小雅被我们匆忙的动作弄醒,
她看到那缕红绳时,眼神闪烁了一下,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跟着我们收拾。
穿过同样死寂的走廊,走下嘎吱作响的楼梯。前台空着,那个古怪的老头不知去了哪里。
我们几乎是逃也似的冲出了旅馆的大门。外面天色已经亮了些,但依旧阴沉。雨停了,
山林间弥漫着湿重的雾气。那棵老槐树静静地立在院中,枝叶上挂满了水珠,
像无数冰冷的眼泪。我们不敢多看,径直跑向停在路边的车子。李悦发动汽车,
引擎发出一阵沉闷的轰鸣,然后猛地蹿了出去。山路蜿蜒,雾气越来越大,能见度很低。
李悦开得很快,几乎是凭着感觉在往前冲。车厢里没有人说话,
只有粗重的呼吸声和车轮碾过湿滑路面的声音。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按照来时的记忆,
这个时间早该驶出这片山区,看到山脚的村镇了。
可窗外依旧是望不到头的盘山路和浓得化不开的雾气。“不对劲……”林晓晓扒着车窗,
声音发颤,“这条路,我们是不是刚才走过?旁边那块像蛤蟆的石头,我好像见过三次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我也注意到了,路边的景致确实有种令人不安的熟悉感。
“别自己吓自己!”李悦低吼一声,但车速明显慢了下来,她的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又开了大概十分钟,当那块蛤蟆形状的石头第四次出现在视野里时,
绝望像冰水一样浇遍了全身。李悦猛地踩下刹车,车子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停在了路中间。
前方,雾气稍微散开的地方,露出了那栋灰扑扑的三层小楼,
以及楼前那棵巨大、沉默的槐树。我们……又回来了。车子像一头疲惫的野兽,喘着粗气,
停在了“槐下旅馆”的门口。绝望如同冰冷的黏液,糊住了每个人的口鼻,让人窒息。
我们瘫在座椅上,没有人说话,只有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的声音。最终还是李悦先动了,
她猛地推开车门,几乎是跌撞着冲回了旅馆。我们跟在她身后,
再次踏入那昏暗、霉味弥漫的大堂。那个穿着灰布褂子的老头,依旧坐在前台后面,
低垂着头,仿佛我们从未离开过。算盘珠子在他枯瘦的手指下,
发出单调而规律的“噼啪”声。“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悦冲到前台,
双手用力拍在木质台面上,声音因为恐惧和愤怒而尖锐。老头缓缓抬起头。
他的脸上皱纹密布,像是干裂的土地,一双眼睛却异常浑浊,几乎看不到眼白。他看着我们,
嘴角极其缓慢地向上扯开一个弧度,形成一个僵硬而诡异的笑容。“走不掉的。
”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木头,“槐树喜欢你们……它想把你们永远留下来。
”“你胡说!”林晓晓尖叫起来,眼泪夺眶而出,“什么槐树!你放我们走!
”老头不再理会我们,重新低下头,专注地拨弄着他的算盘,仿佛我们只是几只吵闹的蚊蝇。
他的话语,那平淡却笃定的语气,比任何张牙舞爪的恐吓都更让人胆寒。槐树喜欢我们?
留下来?一种超越现实理解的恐怖攫住了我们。我们失魂落魄地回到二楼房间,锁死了房门,
仿佛这样就能将那无形的威胁隔绝在外。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们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
手机依旧没有信号。我们想过徒步离开,但站在雾气弥漫的山路口,
一种源自本能的恐惧让我们迈不开步子——那条路,我们已经用车轮验证过它的诡异。
我们也想过大声呼救,可这旅馆除了我们和那个老头,似乎再没有别的活物,
窗外只有山林和死寂。希望一点点熄灭,取而代之的是深入骨髓的冰冷和无力感。傍晚时分,
我们发现自己带来的食物和水分量在莫名其妙地减少,像是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悄悄偷走了。
而旅馆里提供的食物,我们谁也不敢再碰。小雅的状态越来越不对劲。
她不再参与我们的讨论,也不再尝试任何逃离的办法,大部分时间只是抱着膝盖,
坐在面对槐树的那扇窗户前,一动不动地望着外面。她的眼神空茫,
嘴里偶尔会发出极轻的、含糊的音节,像是在和谁低语。“小雅?你在跟谁说话?
”我忍不住问她。她缓缓转过头,脸上是一种奇异的平静,
甚至带着一丝恍惚的微笑:“它们……很寂寞。”“它们?它们是谁?”林晓晓惊恐地追问。
小雅却不回答了,又转回头,痴痴地望着那棵槐树。夜幕再次降临,比前一天更加深沉。
旅馆里的温度似乎降低了不少,呵出的气都带着白雾。我们挤在一个房间里,
谁也不敢单独待着。走廊外,偶尔会传来极其轻微的、像是有人踮着脚走路的声音,
但每次我们屏息凝神去听,那声音又消失了。第二天天亮,小雅不见了。
我们找遍了房间、走廊,甚至壮着胆子去了一楼大堂和前院。哪里都没有她的踪影。
那个前台的老头,依旧坐在那里,对我们的焦急询问充耳不闻。就在我们快要崩溃的时候,
李悦指着窗外,发出一声压抑的抽气。院中,那棵老槐树下。小雅站在那里,背对着我们。
她穿着她最喜欢的那条白色连衣裙,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但她的姿态极其僵硬,
像是被什么东西牵引着的木偶。然后,她开始缓缓地、极其不自然地,绕着那棵槐树行走。
一圈,又一圈,脚步虚浮,如同梦游。“小雅!”我们拍打着窗户,大声呼喊她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