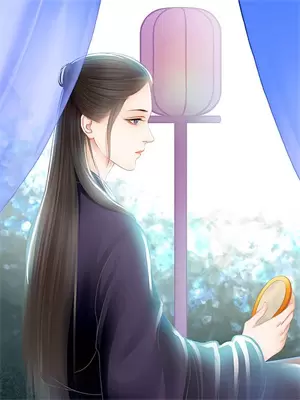阳光斜斜地照进院子,在地上那摊湿漉漉、边缘模糊的拖痕上反射出诡异的光。
我看着那痕迹,从门口一直蜿蜒到院墙的阴影下,
像某种巨大的、无骨的软体动物爬行过的路径。胃里一阵翻滚,我扶着门框,
剧烈地干呕起来,却只吐出一些酸水。噩梦没有结束。它从锦华苑的水泥牢笼,
延伸到了这间看似与世隔绝的平房,甚至钻入了我脚下的土地。逃?
只是一个可笑的自欺欺人。我就像掉进沥青坑的猎物,越是挣扎,陷得越深。
求生的本能是顽强的,即使明知希望渺茫。我强迫自己站起来,用院子里井水泼在脸上,
冰冷的刺激让我稍微清醒。必须离开这里。这个院子已经不再安全,
门外的“东西”可能还在附近徘徊,地下的挖掘声不知何时会再次响起。
我没有多少东西可收拾。几块干硬的面包,两瓶水,
还有那点皱巴巴的、可能已经“失效”的现金。我把它们塞进一个破旧的帆布包里,
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只住了一晚的、短暂的“避难所”,然后深吸一口气,
猛地拉开了那扇布满裂纹的木门。门外空无一人,只有清晨微凉的空气和胡同里惯有的寂静。
我侧耳倾听,没有异常声响。我咬咬牙,低着头,快步走了出去,不敢回头看那地上的拖痕,
也不敢看向院墙的阴影。我必须去人多的地方。虽然我可能是个“污染源”,
会引来不必要的注意,但至少,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人群之中,
那些“东西”或许会有所顾忌?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可能增加一点点生存几率的办法。
我专挑大路走,避开狭窄无人的小巷。早高峰的城市开始苏醒,车流人流逐渐增多。
但我很快发现,情况比我想象的更糟。我试图融入人群,
但周围的人似乎都在下意识地避开我。不是明显的躲闪,而是一种微妙的、不经意的疏离。
我走过时,交谈声会短暂停顿,目光会闪烁移开。仿佛我身上带着一种看不见的寒气,
让靠近的人本能地感到不适。我走到一个公交站,想坐车去更繁华的市中心。公交车进站,
门打开。我跟着人群向前,但当我抬脚要踏上车门时,那司机,一个面色疲惫的中年男人,
突然皱紧了眉头,猛地按下了关门按钮!车门在我面前“哐当”一声合拢,差点夹到我。
公交车喷出一股黑烟,驶离了站台。我愣在原地,看到车上的乘客透过车窗看我,
眼神里带着困惑、警惕,甚至……一丝厌恶。我不是错觉。这种排斥是真实存在的。
我所携带的“污染”,正在影响周围人对我的感知和反应。
我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被无形屏障隔开的孤岛。我不能坐车了。我只能靠双腿。
我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地走着,饥饿和疲惫不断侵袭。我看到一家早餐店,
热气腾腾的包子和豆浆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我走过去,掏出现金。“两个肉包,一杯豆浆。
”我的声音干涩。老板娘熟练地装袋,接过我的钱。她的手指触碰到钞票时,微微顿了一下,
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别扭。她没说什么,找了零钱给我。我拿着食物,
走到不远处的街心花园,找了个没人的长椅坐下。我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包子——味道不对。
不是馊了,也不是调料的问题。而是……一种难以形容的……“空洞感”。仿佛食物的本质,
它的香气和味道,被某种东西抽离了,
只剩下寡淡的、如同嚼蜡般的口感和一股隐隐的……类似墙灰的涩味。我又喝了一口豆浆。
同样如此,温热,但毫无豆香,只有一种令人作呕的粘稠感和若有若无的腐败气息。
不是食物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的感官,或者我与这个世界最基本的连接,
正在被扭曲、被“污染”。我无法再正常地品尝食物,
无法再从最基本的生存活动中获得慰藉。绝望感更深了。
这是一种比直接的恐怖更残忍的折磨。它正在一点点剥夺我作为“人”的体验。
我强迫自己咽下那些味同嚼蜡的食物,维持着最低限度的体力。我必须移动,不能停下来。
我走过商业街,橱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但却仿佛隔着一层毛玻璃,变得不真实。
广告牌上的明星笑脸,看起来扭曲而诡异。城市的喧嚣声传入耳中,也变得模糊、失真,
像是从水下传来。我开始出现幻听。不是墙里的刮擦声,
而是更细微的、仿佛无数人低语的声音,混杂在车流和人群的噪音里,听不清内容,
但充满了痛苦和恶意。我的视线也开始出现问题。
眼角的余光总是捕捉到一些快速闪过的、模糊的黑影,但当我定睛去看时,又什么都没有。
街边建筑物的阴影里,似乎总有什么东西在蠕动。我知道,这不是幻觉。
这是那种“污染”在我身心深处蔓延的迹象。我的精神防线,正在逐步崩溃。下午,
我实在走不动了,瘫坐在一个地铁站出口的台阶上,看着人来人往。每个人都行色匆匆,
有着明确的目的地,他们的生活是连续、正常的。而我,像一个卡在现实缝隙里的bug,
一个正在被世界规则排斥和修正的错误。一个穿着时髦的年轻女孩边看手机边从我面前走过,
没注意脚下,差点绊倒。我下意识地伸手想扶她一下。我的手指并没有碰到她。
在即将接触的瞬间,那女孩像是触电般猛地缩回手臂,脸上露出极度惊恐和厌恶的表情,
仿佛我是什么剧毒污秽之物。她甚至没看清我的脸,就尖叫着跑开了,引来周围一片侧目。
我僵在原地,伸出的手缓缓垂下。那种被整个世界彻底抛弃的感觉,达到了顶点。
连最基本的、无意识的善意接触,都成了不可能。我真的已经……不再属于这里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夜晚,是它们活动的时间。我必须找个地方躲起来。
酒店、旅馆肯定不行,我的身份证是禁忌。桥洞?公园?那些地方更不安全。我忽然想起,
城市里有一些废弃的工厂或者待拆迁的楼房。那里没有人,
或许……也没有那么快的被“污染”?至少,不会波及无辜。我用最后一点力气,
凭着模糊的记忆,向城市边缘的一片老工业区走去。那里有很多废弃的厂房。
我找到一栋半塌的砖混结构楼房,窗户大多破碎,里面堆满了垃圾和碎砖块。
我摸索着爬上二楼,找到一个相对完整的、没有窗户的房间角落,蜷缩起来。
这里充满了尘土和霉菌的味道,但奇怪的是,这种纯粹的破败腐朽,
反而比外面那个正在被无形之力扭曲的“正常”世界,让我感到一丝诡异的……安心。
因为这里本就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被再破坏的了。我靠在冰冷的砖墙上,
疲惫和困意如同潮水般涌来。我知道不能睡,但眼皮沉重得无法抬起。
就在意识即将模糊的边界,我仿佛又听到了那细微的、来自地底的刮擦声。很遥远,很轻微,
但确定无疑。嗤啦……嗤啦……它们还在。一直跟着我。这一次,我没有感到特别的恐惧,
只剩下一种麻木的接受。也许,我的结局,就是在这无人知晓的废墟角落里,静静地等待着,
被来自地下的东西,或者被自身蔓延的“污染”,彻底吞噬。在陷入黑暗前,
我最后一个模糊的念头是:陈老头说的“塔醒了”,或许……不是指锦华苑那栋楼。
而是指……这座城市本身……或者说,
支撑着这座城市正常运转的某种基础规则……正在苏醒或者说崩坏?而我,
是第一个……也是最能清晰感受到这种变化的……祭品。意识在黑暗的泥沼里沉浮。
废弃楼房的冰冷透过单薄的衣服渗入骨髓,但比这更冷的,
是那种无处不在的、被整个世界抛弃的孤绝感。饥饿和干渴像两只小兽,
啃噬着我的胃和喉咙,但更强烈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虚脱,让我连抬起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欠奉。
我没有完全睡着,始终维持着一种半昏迷的警觉。地底那细微的刮擦声似乎消失了,
或者只是被我沉重的呼吸和心跳声掩盖。废墟里死一般寂静,只有风穿过破窗的呜咽,
像无数冤魂在低语。不知过了多久,一丝微弱的光线从没有窗框的洞口照进来,
落在布满灰尘的地面上。天,又亮了。我还活着。又一个夜晚,熬过去了。但活着,
意味着要继续面对这无休止的折磨。求生的本能像一点残存的火星,在绝望的灰烬里闪烁。
我不能死在这里,像一堆无人问津的垃圾。就算要死,我也要……弄明白一些事情。
陈老头最后的话,超市大妈的传闻,档案馆的记载,
还有我亲身经历的一切……像散落的拼图碎片。我必须把它们拼凑起来,
哪怕最终拼出的是更恐怖的图景,也比现在这样不明不白地腐烂强。我需要信息。
需要知道外面到底变成了什么样。锦华苑之后,有没有发生什么异常事件?新闻?网络?
网络……我的手机已经报废了。但我可以去网吧。那种地方鱼龙混杂,管理松散,
或许对身份核查没那么严格。而且,我需要一个能连接外部世界的信息渠道,
哪怕只是单向的。这个念头给了我一丝微弱的力量。我挣扎着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镜子里如果这里有镜子的话的我,一定像个流浪汉,不,比流浪汉更糟,眼神空洞,
面色灰败,带着一种被无形之物侵蚀后的腐朽气息。我走出废墟,重新踏入晨曦中的城市。
阳光依旧,但在我眼中,所有的色彩都蒙上了一层灰翳,仿佛整个世界正在慢慢褪色、变质。
路上的行人依旧对我避之不及,那种无形的排斥力场似乎更强了。我低着头,
尽量避开人群的目光,凭着记忆寻找着便宜的网吧。终于,在一个城中村的狭窄巷子里,
我找到了一家门面破旧、招牌闪烁的“极速网吧”。推开门,
一股浓重的烟味、泡面味和汗味混合的气浪扑面而来。灯光昏暗,
几十台电脑前坐满了形形色色的人,大多沉浸在游戏世界里,没人注意我的到来。
我走到柜台,哑着嗓子对那个正在玩手机的网管说:“开台机子。
”网管头也没抬:“身份证。”我的心一沉。“忘带了,能通融一下吗?我多给点钱。
”我掏出身上最后一张看起来还算“正常”的百元钞票。网管这才抬起眼皮,
懒洋洋地瞥了我一眼,又瞥了瞥钞票,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嫌恶,但还是接过钱,
扔给我一张手写的纸条,上面写着一串数字:“角落那台,别惹事。”我松了口气,
看来金钱的“污染”程度,还没超过他对收入的渴望。
我走到角落那台满是油污的电脑前坐下,开机。电脑运行缓慢,嗡嗡作响。
我急切地打开浏览器,首先搜索本地的新闻网站。页面加载缓慢,
头条新闻多是些无关痛痒的市政工程和娱乐八卦。
我输入“锦华苑”、“异常”、“灵异”等关键词,
跳出来的结果大多是一些陈年旧闻或明显编造的故事,
没有任何关于昨晚那栋楼异动的新报道。被压下去了?还是……根本没人注意到?或者,
注意到了,但消息被严格封锁?我不甘心,
又尝试搜索“集体幻觉”、“地底怪声”、“不明物体”等更宽泛的词条。结果依然寥寥,
偶尔有几个本地论坛的帖子,抱怨最近睡眠不好、总做噩梦,或者宠物行为异常,
但都淹没在海量的信息中,没有引起任何重视。难道……只有我能感觉到?
这种“污染”的显现,是因人而异的?还是说,它的影响是渐进的,
目前还处于非常初级的、仅针对我这个“源头”或“焦点”的阶段?
一种更深的寒意笼罩了我。如果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经历这场噩梦,那是否意味着,
我连寻求理解和帮助的可能都没有了?我深吸一口气,尝试登录我自己的社交账号。
密码错误。连续几次后,账号被暂时锁定。我尝试用密保邮箱找回,
系统提示“安全验证失败”。我被从自己的数字身份里踢出来了。
就像我的实体身份被限制一样,我的网络身份也被某种力量“抹除”或“隔离”了。
绝望再次涌上心头。我像个幽灵,游荡在现实和虚拟世界的边缘,无法真正触及任何一方。
我烦躁地关掉浏览器,目光无意识地扫过电脑屏幕右下角的时间日期。等等……日期?
我的心脏猛地一跳!屏幕上显示的日期……不对!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搬进锦华苑是五天前。
经历了一夜的恐怖,逃到旧城区住了一晚,又在废墟熬了一夜。
今天应该是……应该是搬进锦华苑后的第七天早上!
但屏幕右下角清晰地显示着——搬进锦华苑后的第五天下午!怎么可能?!
我丢失了两天时间?是极度恐惧和疲惫导致的记忆混乱?
还是……在我昏迷或者半昏迷的时候,时间真的被某种力量扭曲了?那座“塔”的影响,
已经涉及到了时间的层面?冷汗瞬间浸透了我的后背。如果连时间感都变得不可靠,
那我还能相信什么?就在我盯着日期,心神剧震之时,电脑屏幕突然毫无征兆地一黑!
不是断电,主机还在运行,风扇还在响。但屏幕彻底黑了,像一块深不见底的墨玉。紧接着,
漆黑的屏幕中央,开始缓缓浮现出一些……东西。不是图像,也不是文字。
而是一些扭曲的、不断变化的……暗影和线条。它们蠕动着,交织着,
逐渐勾勒出一个模糊的……轮廓。那轮廓……越来越清晰……像是一栋楼。
一栋高耸的、现代化的公寓楼。锦华苑!屏幕上的“锦华苑”轮廓周围,
弥漫着浓稠如墨的黑暗。而在楼的表面,墙壁上,
开始浮现出无数细小的、挣扎的……人形阴影!密密麻麻,如同附骨之疽!同时,
一股低沉的、仿佛来自地底深渊的呜咽声,竟然从电脑的音箱里传了出来!虽然音量不大,
但那熟悉的、令人灵魂颤栗的旋律,我死也不会听错!而在这幅恐怖的动态画面中,
在那栋被黑暗和怨灵包裹的楼的顶层,一个窗口,突然亮起了……微弱的、血红色的……光。
那光芒闪烁了几下,然后,一个极其模糊的、干瘦的……人影轮廓,出现在那个窗口后面。
他……或者说“它”……似乎在缓缓地……抬起手。指向屏幕之外。
指向……正在看着屏幕的我。一股无法形容的冰冷瞬间攫住了我全身的血液!
我猛地向后一仰,连人带椅子翻倒在地,发出巨大的声响。网吧里有人被惊动,
不满地咒骂着看过来。网管也站起身,皱着眉头走向我。但我顾不上了!
我手脚并用地从地上爬起来,
惊恐地看着那台已经恢复正常的电脑屏幕——它显示着Windows的默认桌面,
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不!不是幻觉!那呜咽声似乎还在我耳边回荡!
那个窗口后的血色人影!它在向我示警?还是在……召唤我回去?网管走到我面前,
语气不善:“喂!你搞什么鬼?”我脸色惨白,浑身被冷汗湿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只是指着那台电脑,嘴唇哆嗦着。网管疑惑地看了看电脑,又看了看我,
眼神里的嫌恶变成了看神经病一样的警惕:“电脑没问题!你是不是吸了什么东西?赶紧滚!
别在这儿发疯!”我像是获得了特赦,连滚爬爬地冲出了网吧,
重新跌入外面浑浊的阳光和空气里。心脏疯狂跳动,几乎要冲破胸腔。日期错乱。
直接的精神污染通过网络显现。还有……那个窗口后的血色人影……是陈老头吗?
他还以某种形式“存在”着?他在警告我?还是说……那是更可怕的东西,
伪装成他的样子引诱我?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只知道,
情况远比我想象的更诡异、更深入。这场灾难的规模和性质,
可能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范畴。我瘫坐在网吧门口的马路牙子上,看着车来车往,
看着行色匆匆的路人。世界依旧在运转,但它的根基,或许早已被蛀空。而我,
是唯一能听到大厦将倾前,那些细微崩裂声的人。或者,我本身就是那第一道裂痕。接下来,
我该去哪里?还能去哪里?回锦华苑?那是自投罗网。继续流浪?
迟早会被这种无形的侵蚀逼疯,或者被地下的东西挖出来。巨大的迷茫和绝望,如同永夜,
笼罩了我。就在这时,我的目光无意间扫过马路对面的一家小店。
那是一家看起来极其普通的……殡葬用品店。橱窗里摆着花圈、骨灰盒,
还有……一些纸扎的童男童女、金山银山。我的目光,
定格在了那些纸扎人空洞、惨白的脸上。一个荒谬绝伦、却又带着一丝诡异和理性的念头,
如同闪电般划过我几乎停滞的大脑。如果……现实的规则已经失效。
如果……科学和理性无法解释正在发生的一切。那么……是否意味着,
某些早已被现代人遗忘的、更古老、更……“不科学”的规则,开始重新起作用了?
比如……祭祀?比如……与“另一个世界”沟通的方法?这个想法让我不寒而栗,
却又像毒蛇一样,缠绕上我的心。马路对面,那家殡葬用品店的橱窗里,
纸扎的童男童女咧着鲜红的嘴唇,空洞的眼睛仿佛正穿透喧嚣的街道,直勾勾地盯着我。
它们脸上那种程式化的、诡异的笑容,在此刻的我看来,竟然比任何狰狞的鬼脸更令人胆寒。
与“另一个世界”沟通的方法?这个念头像一颗有毒的种子,一旦落下,
便开始疯狂汲取我内心深处的绝望和恐惧作为养料,迅速生根发芽。
科学和理性已经将我抛弃,现实的规则正在我周围扭曲、崩坏。那么,
那些被视为迷信、愚昧的古老方法,
会不会是唯一可能触及真相、甚至……寻求一线生机的途径?我知道这想法疯狂至极,
无异于饮鸩止渴。但一个快要溺死的人,连一根稻草都会拼命抓住,
哪怕那稻草本身也通往更深的水底。我没有立开过马路。那个念头太危险,我需要……准备,
或者说,我需要被逼到真正的绝境,才会跨出那一步。我站起身,继续漫无目的地游荡。
饥饿和口渴像火焰一样灼烧着我的内脏。我尝试着再次用现金购买食物,但结果比之前更糟。
便利店的收银员接过我的钱时,手指像是被烫到一样缩回,钞票从他手中飘落在地。
他脸色发白,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恐惧和厌恶,仿佛我递过去的不是钱,
而是什么污秽不堪的东西。“拿走!快拿走!你的钱……你的钱不对劲!”他尖声叫道,
引得店里的其他顾客都看了过来。那些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鄙夷,警惕,排斥。
我像个瘟疫源,被正常的世界彻底孤立了。我捡起地上的钱,仓皇逃离。我知道,
通过正常渠道获取生存物资的路,已经彻底断了。傍晚,我躲进一个公园的公共厕所里,
拧开水龙头,贪婪地灌了几口带着漂白粉味的自来水。冰冷的水暂时缓解了喉咙的灼烧感,
但胃里的空虚和全身的虚弱感有增无减。天色暗了下来。公园里的路灯次第亮起,
但光线似乎无法完全驱散角落里的黑暗,那些阴影看起来比白天更加浓重,
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其中蠕动。我知道,我不能再待在外面了。夜晚是它们的主场。
我必须找个地方藏起来,哪怕只是一个桥洞,一个垃圾站。就在我准备离开厕所时,
一阵细微的、熟悉的刮擦声,再次传入我的耳朵。嗤啦……嗤啦……这一次,
声音不是来自地底。而是来自……厕所隔间的门板后面。我全身的血液瞬间凝固了。
我屏住呼吸,一动不敢动,眼睛死死盯着那几个紧闭的隔间门。声音来自最里面的那一间。
一下,又一下,缓慢而持续,就像……就像最初在锦华苑的夜里听到的那样。用指甲,
在木质门板的内侧,缓慢地刮擦。是谁?是流浪汉?还是……我不敢想下去。
我慢慢地、极其缓慢地向厕所门口挪动,生怕发出一点声响惊动里面的东西。
就在我即将摸到门口的时候,最里面那间隔间的门板下方缝隙里,
突然渗出了一小滩……暗红色的、粘稠的液体。那液体缓缓蔓延开来,
带着一股熟悉的、令人作呕的……墙灰和腐朽的气息。隔间里的刮擦声,戛然而止。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其轻微的、像是湿漉漉的东西在地上爬行的……窸窣声。那声音,
正朝着隔间门的方向过来。我魂飞魄散,再也顾不上掩饰,猛地转身,撞开厕所门,
发疯似的冲了出去,一头扎进公园浓重的夜色里。我拼命地跑,不敢回头,肺部火辣辣地疼,
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我听到身后似乎有东西拖沓着追来的声音,
还有那种湿漉漉的摩擦声。我慌不择路,冲出了公园,冲进了一条昏暗的小巷。
巷子深处堆满了垃圾箱,散发着馊臭的气味。我看到一个半开的、巨大的绿色垃圾箱,
几乎是本能地,我掀开盖子,不顾一切地跳了进去,然后将盖子拉上,
只留下一条缝隙用于呼吸。垃圾箱里恶臭扑鼻,腐烂的菜叶和不明粘液沾了我一身。
但我顾不上了,我蜷缩在令人作呕的废弃物中间,透过缝隙,惊恐地望向外面。几秒钟后,
一个……东西……出现在了巷子口。我看不清它的具体形态,因为它似乎没有固定的形状,
更像是一团蠕动的、浓稠的黑暗。它移动的方式很奇特,不是走,而是……流淌?贴着地面,
悄无声息地滑入小巷。它经过我藏身的垃圾箱时,略微停顿了一下。我死死捂住嘴,
连心跳都几乎停止。我能感觉到一股冰冷的、带着强烈腐朽气息的“视线”,扫过了垃圾箱。
但它没有停留。它继续向巷子深处流淌而去,消失在更深的黑暗中。我瘫软在垃圾堆里,
劫后余生的虚脱感让我几乎晕厥。但比恐惧更强烈的,是那种深入骨髓的耻辱和绝望。我,
一个曾经的程序员,一个现代社会的所谓“精英”,现在像一只老鼠一样,
躲在肮脏恶臭的垃圾箱里,躲避着无法理解的恐怖。这一刻,所有的犹豫和侥幸都消失了。
理性?科学?它们在我跳进垃圾箱的那一刻,已经彻底死亡。我艰难地从垃圾箱里爬出来,
带着一身污秽,踉跄着走在午夜无人的街道上。我的目光,
再次投向那个方向——那家殡葬用品店。它已经关门了,橱窗里的纸扎人在惨白的月光下,
笑容显得更加诡异。但我需要的,不是店里的商品。我需要的是……知识。
是关于如何与“那个世界”打交道的、被遗忘的、可能记录在某种古老书籍里的知识。
图书馆?或许有,但太正式,可能找不到我需要的“偏门”。旧书摊?
或者……那种专门售卖风水、玄学书籍的小店?我在城市的老区里游荡,像一具行尸走肉。
天快亮时,我终于在一个极其偏僻的、即将拆迁的街区角落,找到了一个还没开门的旧书店。
橱窗里堆满了泛黄的旧书,其中几本的封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