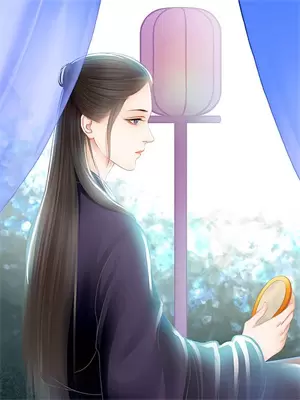1 酷暑惊魂二零一二年的重庆,夏天来得格外早,也格外凶猛。进了六月,
日头便一天毒似一天,悬在头顶,白晃晃地炙烤着大地。沙坪坝区井口镇这一片,
新修的柏油马路被晒得滚烫发软,踩上去,鞋底仿佛都要黏住,滋啦一声,
带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焦糊味。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近乎凝固的热浪,
知了在道旁稀疏的桉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更添了几分焦躁。郝姐的五金厂,
就在这酷暑中搬进了新址。厂房是租的,原先的厂子经营不善倒了,地方还算宽敞。
院墙新刷了天蓝色的油漆,在烈日下显得有些刺眼。车间里,
新购置的冲床、剪板机一字排开,散发着机油和金属的混合气味。工人们忙进忙出,
搬运着原料和工具,汗珠子摔在地上,立刻就成了一个小湿印,旋即又被蒸发殆尽。
郝姐站在车间门口,看着眼前这番忙碌景象,心里头本该是充满希望的——搬新地方,
添新设备,指望着生意能更上一层楼。可不知怎的,看着那新刷的、过于鲜亮的蓝墙,
她心里头总隐隐约约觉得有些不踏实,那蓝色像一块冰,搁在燥热的空气里,
反而衬得周遭更加闷得慌。这感觉没来由,她也只当是搬迁劳累所致,并没十分往心里去。
然而,这隐隐的不安,很快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砸得粉碎,露出了狰狞的本相。
那是七月里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下午,大概三点钟光景,日头正毒,车间里虽然开着吊扇,
但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混着金属碎屑和汗水的气味。机器的轰鸣声是这方天地的背景音,
工人们早已习惯。突然,“哐当”一声闷响,从冲床那边传来,声音比平日里短促,
也沉浊了许多,像是铁锤砸进了湿棉花里,带着一种不祥的顿挫感。
郝姐当时正在隔壁的办公室里核对一批新订单的数目,听到这异样的声响,心里咯噔一下,
账本上的数字瞬间模糊了。她几乎是弹起来的,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划出刺耳的噪音。
也顾不上穿好那只刚才因天热而脱掉的半高跟凉鞋,趿拉着就冲出了办公室,
心里头像揣了只兔子,砰砰直跳。车间里的机器声似乎稀疏了些,
不少工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计,朝着冲床那边张望。郝姐拨开人群,
一眼就看见了蹲在地上的小王。那孩子才二十出头,从四川农村来的,平时腼腆得很,
干活却舍得下力气。此刻,他蜷缩在地上,左手死死地攥着右手手腕,脸色惨白如纸,
嘴唇没有一丝血色,豆大的汗珠从额角滚落,混着脸上的油污,划出一道道痕迹。
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但浑身都在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最扎眼的,
是那从他指缝里不断渗出的鲜血,一滴,两滴,连成了线,落在沾满黑色油污的水泥地上,
洇开一小片暗红。就在他脚边不远,一块废弃的铁皮料上,
赫然躺着一小截东西——是他的右手小指!断口处参差不齐,白森森的骨茬露在外面,
周围是模糊的血肉,看着就让人头皮发麻,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咋回事?!咋弄的?!
”郝姐的声音都变了调,冲上前蹲下,想看看伤势,又不敢贸然去动那只手。
旁边一个老师傅惊魂未定地说:“就……就刚才冲床下来,
好像手没抽利索……”“别愣着了!快!快送医院!”郝姐猛地回过神,声音带着哭腔,
也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她一把搀起几乎虚脱的小王,
另一只手胡乱抓过办公桌上那个装钱的挎包,也顾不得血污,
半抱半拖地把小王往停在院子里的那辆旧桑塔纳里塞。小王的身子冰凉,
攥住她胳膊的手就像铁钳一样,指甲因为用力而深深掐进她肉里,但他依旧没哭,
只是喉咙里发出压抑的、野兽般的呜咽。去医院的路上,郝姐把车开得飞快,
闯了几个红灯她都记不清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保住那根手指!后视镜里,
小王歪靠在座椅上,眼睛紧闭,脸色白得吓人。窗外的热风灌进来,
吹不散车厢里浓重的血腥味和绝望。到了医院,急诊室的医生检查后,说指头断得还算整齐,
可以尝试接上,但手术有风险,而且术后恢复期长,费用也不菲,让家属赶紧准备钱。
郝姐想都没想,立刻跑到缴费处,把挎包里准备给供应商结账的五万块钱先垫了上去。“治,
无论如何要治好,钱我想办法!”她对医生反复说着。小王家里情况困难,父亲早逝,
老家还有个瘫痪在床的母亲,他是家里的顶梁柱。郝姐心里清楚,这娃儿不容易。住院期间,
她让厂里食堂天天熬了骨头汤、鸡汤送去,又托人多方打听,
联系上了他在老家的一个远房堂哥。她心想,都是出门在外讨生活的人,能帮一把是一把,
只要人没事,比什么都强。小王的伤势恢复得还算顺利,手指接上了,
虽然医生说以后功能肯定会受影响,但总比彻底没了强。郝姐稍稍松了口气,
开始着手处理后续的赔偿事宜。她私下里也咨询过相熟的律师,按照工伤赔偿标准,
加上已经垫付的医药费、后续的康复费用,满打满算,十万出头应该就能覆盖了。
可等到小王的那个堂哥从老家赶过来,事情就一下子变了味。那堂哥约莫四十岁年纪,
穿着件皱巴巴的西装,眼神里透着精明的算计。他一来,没先关心小王的伤势恢复如何,
直接把郝姐拉到一边,开口就要二十万。“郝老板,”堂哥吐着烟圈,语气倒是平和,
话却硬得很,“我兄弟这可不是蹭破点皮,是断了一根手指头!俗话说‘十指连心’啊,
这以后就是个残废了,干活受影响不说,讨老婆都难!二十万,
这还是看在你郝老板之前垫付医药费、照顾他的份上,要按我说,三十万都不多!
”郝姐一听,心就凉了半截。她试着解释:“他大哥,你的心情我理解。可厂里刚搬过来,
买设备、装修、进货,投入了一大笔钱,现在资金周转确实困难。再说,
这赔偿也有国家的标准……”“标准?那是死的,人是活的!”堂哥打断她,
声音提高了八度,“我兄弟一辈子的事,能用那点标准衡量?郝老板,你要觉得为难,
那咱们就只好法院见了。不过话说前头,到时候判下来,可就不止这个数了,
还得加上诉讼费、误工费啥的。”郝姐又去找小王谈,希望这娃儿自己能有点主见。
可小王坐在病床上,脑袋几乎埋进了胸口,任凭郝姐怎么说,他只是一言不发。
他堂哥站在旁边,眼神像刀子一样。最后,
小王才蚊子哼哼似的挤出一句:“俺……俺听哥的。”谈判彻底僵住了。郝姐心寒之余,
也只好硬着头皮走法律程序。法院的判决下来,果然和律师预估的差不多,
除去郝姐已经垫付的医药费,厂里再赔偿小王八万元。算下来,
郝姐为这事前后花了十三万左右。拿着判决书,郝姐心里五味杂陈。钱是赔了,
可这心里头的疙瘩却结下了。在法院门口,小王的堂哥脸色铁青,指着郝姐的鼻子,
恶狠狠地撂下一句话:“行!郝老板,你够狠!咱们走着瞧,这事儿,没完!
”当时郝姐只当他是输了官司,面子上挂不住,说的气话。加上厂里一堆事等着处理,
她也没太往心里去。赔偿款尽快给了对方,只盼着这事儿能像翻书一样,赶紧翻篇。
2 诡异开端可她万万没想到,这句“没完”,竟然像一句恶毒的诅咒,
悄然拉开了五金厂一连串诡异事件的序幕。先是快到月底盘存的时候。老工人张师傅,
在车间角落搬一块不太重的钢板时,脚下莫名其妙地一滑,整个人仰面摔倒,
那块钢板不偏不倚,正好砸在他的脚背上。送到医院一查,脚骨骨折。
张师傅在厂里干了十几年,是出了名的稳当人,车间地面也每天都打扫,怎么就会滑倒?
而且偏偏就被钢板砸中?郝姐刚把张师傅这边安顿好,没消停两天,
夜班负责操作一台老式铣床的李姐又出了事。李姐是厂里的老员工,技术娴熟,
闭着眼睛都能操作那台机器。可那天晚上,她就像中了邪一样,明明已经关了电源,
手却鬼使神差地伸进了尚未完全停稳的夹具里,手指被硬生生夹了一下,虽然没断,
但也是一片乌紫肿胀,医生说至少得休息半个月。
如果说这两次还能勉强归咎于意外和操作失误,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就彻底让人无法用常理来解释了。一个周末的晚上,加班赶一批急活。
行车工小赵操作着行车,吊着一捆沉重的角钢,平稳地移向指定位置。
底下两个工人正在清理场地。突然,“蹦”的一声脆响,成年人拇指粗细的钢丝绳,
毫无征兆地从中间断裂了!那捆角钢带着风声轰然砸落,距离底下干活的两个工人,
仅仅一步之遥!沉重的钢材将水泥地面砸出了一个小坑,飞溅起的碎石屑打在旁边的机器上,
噼啪作响。整个车间瞬间死寂,所有人都被这惊魂一幕吓傻了。半晌,
才有人颤颤巍巍地围上去检查。那断裂的钢丝绳茬口簇新,明显不是正常磨损老化所致,
就像是被人用利刃齐齐割断了一半,剩下一半承受不住重量才崩开的。
可谁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割行车钢丝绳?更何况,那位置那么高,寻常人根本够不着。
接二连三的怪事,像阴云一样笼罩了整个五金厂。工人们开始窃窃私语,人心惶惶。有人说,
夜里加班的时候,总觉得车间角落里有人影晃动,走近了又什么都没有。有人说,
听见机器自己发出奇怪的响声,像是有人在轻轻敲打。更有人煞有介事地嘀咕,
说这新厂房以前就不干净,怕是冲撞了什么“东西”。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
开始有工人悄悄找郝姐结清工资,宁可不要这个月的奖金,也要离开这个“邪门”的地方。
订单交货期一天天逼近,客户催货的电话一个接一个,语气越来越不耐烦。
郝姐嘴上都急起了燎泡,白天强打精神处理各种烂摊子,晚上躺在厂里值班室那张小床上,
却辗转难眠。夜深人静时,车间那边似乎总传来一些若有若无的声响,
像是有人穿着软底鞋在空旷的车间里踱步,又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轻轻刮擦着铁皮墙壁。
她大着胆子打着手电筒出去查看过几次,手电光柱扫过寂静的机器和堆放的物料,一切如常,
只有她自己的心跳声,在空荡的厂房里显得格外响亮。一种无形的、令人窒息的压力,
让郝姐快要崩溃了。她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镜子里的自己,眼窝深陷,憔悴不堪。
3 神秘张师转折点发生在一个周一的清晨。郝姐早早来到车间,想趁着工人没上班,
再仔细检查一下那台出过事的冲床和行车。当她走到小王当初操作的那台冲床旁时,
目光无意间扫过操作台,心里猛地一紧。操作台上,放着一把老式的老虎钳。
这种钳子平时用得少,一般都放在工具柜里。而此刻,这把钳子却突兀地出现在这里,
钳口微微张开,上面沾着一些黑褐色的、像是灰烬一样的东西。郝姐凑近了些,
闻到一股淡淡的、类似烧糊了的纸钱的味道,若有若无,却直往鼻子里钻。
一股寒意瞬间从脚底窜上脊梁骨。她想起之前一起合伙开厂、后来因家庭原因退出的王姐。
王姐是井口镇本地人,见识广,有一次闲聊时提起过,说镇上以前有位姓张的老师父,
不是寻常意义上的算命先生或神棍,平日里就在家莳花弄草,看起来跟普通退休老人没两样,
但真有遇到“不干净”的事情去找他,他往往能看出些门道。走投无路的郝姐,
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赶紧给王姐打了电话。
王姐听她语无伦次地讲完厂里最近的怪事和那把奇怪的老虎钳,沉默了一会儿,
说:“郝妹子,你别急,我先帮你打听打听。张师父这人有点怪,但你去找他,记住,
态度一定要诚恳,别摆老板架子,也别空手,随便带点时令水果就行。”第二天,
王姐回了信,给了郝姐一个地址,就在镇子东头的一个老家属院里。
郝姐立马买了些新鲜的苹果和香蕉,按照地址找了过去。那是一片很有年头的红砖楼,
楼道里阴暗,弥漫着各家各户做饭的混合香味。找到三楼,门牌号没错,
深绿色的铁皮门虚掩着,留着一条缝。郝姐深吸一口气,轻轻敲了敲门。“进来。
”里面传来一个略显沙哑,但很平稳的声音。郝姐推门进去。屋子不大,
陈设简单得近乎简陋。一张老式的木方桌,两把竹椅,墙上光秃秃的,只挂着一幅泛黄的画,
画上是个身着道袍、仙风道骨的人物,手里捏着一道符,符上隐隐有电光缭绕,
看上去颇有气势。一位头发花白、身形清瘦的老人正坐在桌边,手里端着一个粗瓷大碗,
碗里是清水,他正慢条斯理地往水里撒着小米。这就是张师父了。他抬起头,
目光在郝姐脸上扫了一下。那双眼睛并不像一般老人那样浑浊,反而异常清亮,
像是能一下子看到人心里去。“坐吧。”他指了指对面的竹椅,语气平淡,
“王姐跟我提过了,你厂里不太平?”郝姐把水果轻轻放在桌角,依言坐下。
面对张师父那平静的目光,她这些日子积攒的委屈、恐惧、焦虑一下子找到了宣泄口,
也顾不得什么体面了,从头到尾,把如何搬迁新厂,小王如何出事,赔偿如何谈不拢,
堂哥如何威胁,之后厂里又如何接连发生诡异事故,工人们如何恐慌,
以及那天早上发现的沾着纸灰味的老虎钳……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说到后来,
声音哽咽,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张师父一直安静地听着,没有打断她,脸上也没什么表情,
只是偶尔看一眼手里的水碗。等郝姐说完,他才把那只粗瓷水碗往她面前推了推:“莫慌,
你先看看这个。”只见他从口袋里又摸出一小撮小米,用右手拇指、食指和中指捏着,
双目微闭,嘴唇轻轻翕动,念诵着一段郝姐完全听不懂的咒文。念罢,将指尖的米粒,
轻轻撒入水碗之中。郝姐屏住呼吸,瞪大了眼睛看着。那碗水原本平静无波,米粒落入后,
照理应该缓缓沉底。可奇怪的是,这些米粒非但没有下沉,反而在水面上滴溜溜地旋转起来,
起初很慢,后来越转越快,形成一个小小的漩涡。更诡异的是,这漩涡毫无规律可言,
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时而又像是要散开,就是定不住一个方向,
仿佛有什么无形的力量在干扰着它们。“咦?”张师父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脸上露出一丝凝重。他放下右手,抬起左手,手指开始飞快地变换姿势,
拇指依次掐过食指、中指、无名指的各个指节,最后定格在一个郝姐看不懂的诀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