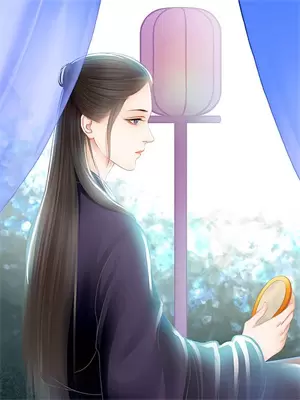地下室的灯很暗,只有一个光秃秃的灯泡。我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手脚被绑着。
绳子勒得很紧,手腕火辣辣地疼。嘴也被封住了。我没哭,也没闹。我看着面前的男人。
他很高,很瘦,穿着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脸上戴着一个最普通的白色面具,
只露出眼睛和嘴巴。他的眼睛很黑,像两个洞,正在看我。他绑架我的时候,动作很利落。
没有多余的话,一块布捂上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就在这里。这里很潮,
有一股发霉的味道。他什么也不说,就那么站着,看了我很久。我被他看得发毛。
我见过很多坏人,我爸生意场上的对手,一个个都比他看起来凶。可他们都没有这双眼睛。
这双眼睛里什么都没有。没有欲望,没有愤怒,就是……空。像在看一件东西。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他一动不动。我腿麻了,身体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冷的。他终于动了。
他走到我面前,蹲下来。我能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松节油味。画画的人才有的味道。
他伸出手,手指很长,骨节分明。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的手指碰了碰我的脸。很凉。
然后,他撕下了我嘴上的胶带。动作很轻。“别喊。”他的声音很低,有点哑。我点点头。
我喊了也没用,这里听起来很偏。“饿吗?”他问。我摇头。他站起来,转身出去了。
铁门被锁上,发出“哐当”一声。我又是一个人了。黑暗里,我拼命回想被绑架的细节。
那辆车,那条路。没用,什么都想不起来。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又开了。
他端着一个托盘进来。一碗粥,还冒着热气。旁边有一杯水。他把托盘放在地上,
推到我面前。“吃。”我的手被绑着。他好像才反应过来,走过来,解开了我手上的绳子。
手腕上一圈深深的红痕。我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指,端起碗。粥是白粥,什么都没放。
我小口小口地喝。他就在旁边看着我吃。我喝完了。他把碗收走,又重新绑上了我的手。
这次,他没走。他在离我两三米远的地方坐下来,靠着墙。我们俩就这么待着。我不说话,
他也不说话。灯光昏暗。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又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实在撑不住,睡着了。睡得很不安稳。半夜,我被冷醒了。睁开眼,
发现身上多了一条毯子。是条很旧的毛毯,有点扎人。他还在那里坐着,姿势都没变。
我看着他的侧影,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他好像……不准备要钱。2第二天,
他进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本书。是一本诗集。他把饭放下,等我吃完,收拾好。然后,
他坐回原来的位置,翻开了书。他开始念诗。是里尔克的。“严肃地看人,是多么累人的事。
”他的声音还是那么低,那么哑,像砂纸磨过木头。地下室里,只有他的声音。我看着他,
觉得这事越来越奇怪了。绑匪给肉票念诗?他念得很慢,很有感情。
好像这些诗是他自己写的一样。念完一首,他就停下来,看着我。
我不知道他要我有什么反应。我只能看着他。我们就这样互相看着。过了很久,
他又念下一首。一天就这么过去了。第三天,还是这样。送饭,念诗,看着我。第四天,
第五天。我快疯了。这种安静,比打我一顿还难受。我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这天,
他念完诗,我终于忍不住了。“你到底想要什么?”我问。我的声音因为很久没说话,
也很哑。他合上书,看着我。“钱吗?你要多少钱?我爸会给你的。”我说。他没说话。
“你说话啊!”我有点崩溃。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我害怕地往后缩。他蹲下来,
面具后的眼睛盯着我。“你觉得,”他慢慢地说,“你值多少钱?”我愣住了。
“我……”“一亿?十亿?”他问。“我不知道。”“你的父亲,”他说,
“是个很厉害的商人。他最懂价值。”我没说话。是,我爸许正国,最懂价值。
我从小就知道,我身上也带着价码。我需要学的才艺,需要交往的朋友,以后需要嫁的人,
都是我这个“价码”的一部分。“他会给你钱的。”我重复了一遍。他笑了。虽然隔着面具,
但我能感觉到他在笑。那笑声,很冷。“我们等等看。”他说。说完,他站起来,走了出去。
从那天起,他不再念诗了。但他还是每天来。送饭。然后就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地看着我。
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我感觉自己像动物园里的猴子。不,连猴子都不如。
猴子还有人给它扔香蕉。我只有一碗白粥。我开始害怕他的注视。那目光,像手术刀一样,
要把我一层一层地剖开。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我闭上眼,都是他那双空洞的眼睛。
我快要被逼疯了。我宁愿他给我一刀。这样无声的折磨,比死还难受。3大概过了一个星期。
他再进来的时候,手里拿的东西变了。不是书。是一个画架,一块画布,还有一箱颜料。
他在我面前,不紧不慢地把画架支好。然后,他搬了张凳子,坐下来。他要干什么?
他拿起画笔,调着颜料。然后,他抬头看我。“别动。”他说。我明白了。他要画我。
我心里一阵恶寒。我见过很多画家。我妈喜欢收藏画,家里有很多名贵的艺术品。那些画家,
看模特的眼神,是审视,是欣赏。可他的眼神不是。他的眼神,是贪婪。
像一个饿了很久的野兽,看到了唯一的食物。他要把我,拆骨入腹,画进他的画里。
我一动不敢动。地下室里,只有画笔摩擦画布的“沙沙”声。他画得很快,很专注。
我甚至觉得,他已经忘了我的存在。他的世界里,只有那块画布。我成了他眼里的颜色,
线条,光影。我不再是我自己。我第一次,这么清晰地感觉到,我成了一件“东西”。以前,
在家里,我爸妈也把我当东西。一件用来联姻的、有价值的、漂亮的“东西”。但那种感觉,
是模糊的。现在,这种感觉,无比清晰。我就坐在这里,看着他把我,一点一点地,
变成颜-料。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的身体已经僵硬了。他终于停了笔。他看着画布,
好像很满意。然后,他抬头看我。“好了。”他说。我松了口气,刚想动一下。“明天继续。
”他又说。我的心又沉了下去。第二天,他来了。第三天,他又来了。每天都是一样的流程。
送饭,画画。我像一个没有灵魂的娃娃,坐在那里,任由他摆布。我开始观察他。
我想从他身上,找到一点破绽。他很高,目测有一米八五以上。他很瘦,手腕的骨头很突出。
他走路没有声音,像一只猫。他身上总有松节油的味道。他从来不在这里上厕所,
也从来不在这里睡觉。这个地下室,只是他关我的地方。他的手很稳,拿画笔的时候,
一点都不抖。可我总觉得,他那平静的外表下,藏着一头快要失控的野兽。有一次,
他画画的时候,一滴颜料滴到了画布外面。是红色的。像一滴血。他的身体,瞬间僵住了。
他死死地盯着那滴红色。我看见他拿画笔的手,在发抖。呼吸也变得很重。地下室的气氛,
一下子变得很危险。我吓得不敢出声。过了好久,他才慢慢地,用布,把那滴红色擦掉。
擦得很用力。好像要擦掉的,不是颜料,是什么别的东西。从那天起,我确定了一件事。
这个人,是个疯子。一个极度压抑的、偏执的疯子。而我,就是他唯一的发泄口。
4时间过得越来越慢。我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这个地下室里,
永远只有那一盏昏暗的灯。我开始分不清,自己是醒着,还是在做梦。有的时候,
我看着他画画,会突然走神。我觉得,我也变成了一幅画。
一幅被困在画框里的、不会动也不会说话的画。他那幅画,快画完了。画布上的我,
穿着被绑架时的那件白色连衣裙。眼神里,有恐惧,有迷茫,
还有一丝我自己都没察觉到的……认命。他把我画得很像。不,比我本人更像我。
他把我心里藏着的东西,全都画了出来。这让我感到害怕。他好像能看透我的灵魂。
画完最后一笔,他站起来,退后几步,端详着自己的作品。很久,很久。然后,他转过头,
看着我。“像吗?”他问。我点点头。他好像很高兴。那双空洞的眼睛里,
第一次有了一点别的情绪。是……满足。一个创造者,对自己作品的满足。
他把画小心翼翼地搬到一边,用布盖好。然后,他拿出了一个东西。一个手机。我的心,
猛地一跳。他要打电话了。他要开始要赎金了。这场诡异的囚禁,终于要进入正题了。
他拨了一个号码。然后,他把手机开了免提,放在我面前的地上。电话通了。“喂?
”是我爸的声音。许正国。冷静,沉稳,永远都那么有威严。听到他声音的那一刻,
我差点哭出来。“许先生。”顾沉开口了。“你是谁?”我爸问。“一个拿了你女儿的人。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我爸的声音,听不出一点情绪波动。“开个价吧。”他说。简单,
直接。像在谈一笔生意。顾沉笑了。“许先生果然是爽快人。”“二十亿。
”顾沉说出了一个数字。一个天文数字。我爸的公司,市值也就一百多亿。二十亿现金,
就是要他的命。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这次,沉默的时间更长。我紧张地屏住呼吸。
“不可能。”我爸终于开口了,“我没有那么多现金。”“那是你的事。”顾-沉说,
“我只要结果。”“你撕票吧。”我爸说。我愣住了。我以为我听错了。“你说什么?
”连顾沉都愣了一下。“我说,你撕票吧。”我爸的声音,像一块冰,“我不会给你二十亿,
去救一个以后只能用来联姻的工具。她不值这个价。”工具。不值这个价。我浑身的血液,
好像都冻住了。“许先生,你很冷静。”顾沉的声音也变冷了。“我是一个商人。”我爸说,
“商人,只看利益。为了一个没有回报的投资,去冒掏空公司的风险,不划算。
”“她是你女儿。”“生意场上,没有父女。”说完,我爸挂了电话。电话里,
只剩下“嘟嘟”的忙音。在死寂的地下室里,响得特别刺耳。我看着地上的手机,
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顾沉也看着手机,没有动。过了很久,他弯腰,捡起手机。
他抬头看我。我看不清他面具后的表情。但我看到,他那双一直很空洞的眼睛里,
有什么东西,碎了。然后,又有什么东西,慢慢地长了出来。是一种……很奇怪的情绪。
不是愤怒。也不是同情。是……兴奋。一种野兽找到了同类的兴奋。他看着我,
一字一句地说:“你看,我说的没错吧。”“他,比我,更懂价值。”5从那天起,
顾沉不再来了。地下室里,只有我一个人。还有那幅盖着布的画。吃的和水,
会有人从门下的小窗口递进来。但我没再见过他。我爸的话,像一把刀,插在我的心上。
他说我是工具。他说我不值那个价。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但我从没想过,
他会这么直白地,在绑匪面前,说出来。他放弃了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我。
我蜷缩在角落里,抱着那条扎人的毛毯。我没有哭。眼泪好像流干了。心里,是空的。
比这个地下室还要空。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天,两天,还是一年,两年。这里没有时间。
我开始出现幻觉。我看见我爸,穿着西装,站在我面前,冷冷地看着我。他说:“知意,
你要懂事。你要为家族的利益着想。”我看见我妈,拿着一本相册,指着上面的男人。
她说:“知意,这个张总的儿子不错,你们见个面吧。对你爸的公司有好处。”我看见他们,
围着我,对我笑。笑得很假。我的世界,成了一个巨大的、华丽的牢笼。而我,
就是笼子里那只供人观赏的金丝雀。现在,这个笼子破了。
我又掉进了另一个更小、更黑的笼子。有什么区别呢?好像也没什么区别。有一天,
我从门外,隐约听到了电视新闻的声音。声音很小,断断续续的。但我听到了几个关键词。
“许氏集团”、“股价稳定”、“千金”、“出国休养”。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狠狠地攥住。
我爬到门口,把耳朵贴在冰冷的铁门上。新闻里的女主持人,
用标准的声音说:“……针对近期许氏集团千金许知意小姐失联的传闻,
许氏集团董事长许正国先生今日公开回应,称其女儿目前正在国外休养,状态良好。
许先生表示,感谢外界关心,但希望不要过度解读,以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受此消息影响,
许氏集团股价今日小幅回升……”我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出国休养。他把我的人生,
我的是死是活,变成了他稳定股价的工具。他早就给我判了死刑。公开地,体面地,
把我“撕票”了。我笑得喘不过气来。原来,我连二十亿都不值。
我只值那“小幅回升”的几个百分点。真可笑。我这一生,就是一个笑话。从那天起,
我不再想逃跑了。逃出去,又能去哪呢?回到那个华丽的牢笼里,继续当我的金丝雀吗?
好像,还不如待在这里。至少,这里只有一碗白粥。没有人会告诉我,我应该做什么,
应该嫁给谁。我开始不吃不喝。我不想活了。死了,就都解脱了。第三天,我饿得头晕眼花,
躺在地上,连动的力气都没有了。铁门,突然开了。顾沉走了进来。他好像瘦了点。
他看到我这个样子,还有门口没动的饭菜,愣住了。他走到我面前,蹲下来。“你想死?
”他问。我没力气回答。他伸出手,捏住我的下巴,强迫我张开嘴。然后,他拿起水杯,
把水往我嘴里灌。我呛得直咳嗽。“我说了,你想死?”他又问了一遍。我看着他。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用尽力气说。他看着我,很久。“有关系。”他说,“你的命,
现在是我的。”“我还没画完。”“在我画完之前,你不能死。”说完,他把我抱了起来。
他的手臂很瘦,但很有力。我像一个破布娃娃一样,被他抱在怀里。
我闻到了他身上那股熟悉的松节油味。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竟然有了一丝……安稳。
很奇怪。我一定是疯了。6他又开始给我画画了。但这次,画的不是我。
他架起了好几块新的画布。每天,都在不同的画布上画几笔。我看不懂他在画什么。那些画,
很抽象,很大胆。颜色很浓烈,线条很扭曲。像一团燃烧的火,又像一个挣扎的噩梦。
我看着他画画,觉得他比以前更疯狂了。他会为了一个颜色,在调色盘上试几十次。
他会盯着画布,几个小时不动一下。有的时候,他会突然暴躁地把画笔扔掉,
嘴里骂着我听不懂的话。但他从来没有伤害我。他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一个只有他,和他的画的世界。我还是坐在原来的位置。我成了他这个疯狂世界里,
唯一的观众。也是唯一的参照物。他每画一会儿,就会抬头看看我。好像在确认,我还在。
然后,再低头继续画。我每天的食物,不再是白粥了。他会给我带牛奶,面包,
有的时候还有水果。他好像,真的怕我死掉。有一天,他画完画,收拾东西的时候,
从口袋里掉出来一个东西。是一个小小的木雕。雕的是一只鸟。翅膀是合拢的,头低着。
像一只正在睡觉的、没有安全感的鸟。雕工很粗糙,像是随手刻的。他很快就发现了,
弯腰捡了起来。我看到,他把木雕握在手心里,握得很紧。好像那是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我没问。我知道,那是属于他世界里的东西。我不想去碰。我爸给我定下的“撕票”期限,
快到了。是顾沉告诉我的。那天,他画完画,突然开口。“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他说。
我心里一紧。“你……”我看着他,“你会杀了我吗?”他没有直接回答。
他反问我:“你怕死吗?”我沉默了。以前,我觉得死亡是解脱。可现在,我不知道。
我看着他,看着他面具后的那双眼睛。我好像,有点不想死了。“我不知道。”我说。
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如果,”他慢慢地说,“你死了。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人,
会像我这样看着你了。”他的声音,有一种奇怪的魔力。“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他们看的,
都不是你。”“他们看的,是你身上的价值,是你背后的家族。”“只有我。”“我看的,
是你。”我的心,跳得很快。他说得对。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看过我。
那种专注的、不带任何杂质的、仿佛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眼神。尽管,
那眼神来自一个绑架我的疯子。“最后一天,会发生什么?”我问。他看着我,很久。
“不知道。”他说,“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他走了。最后一天,快来了。我的心里,
很乱。有害怕,有期待,还有一丝……连我自己都说不清的、奇怪的情绪。7最后一天。
我坐在地下室里,等着。等我的审判。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手心,全是汗。
我不知道他会用什么方式。是刀,还是枪,还是……一根绳子。我想了很多种死的可能。
但每一种,都让我觉得不甘心。我还没有,好好地活过一天。门,开了。我的心,
提到了嗓子眼。我闭上眼睛,不敢看。我听见脚步声。一步,一步,向我走来。然后,
停在了我面前。我等了很久。想象中的疼痛,没有来。我闻到了一股味道。不是松节油味,
也不是血腥味。是一股……很清新的、野花的香味。我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然后,
我愣住了。顾沉站在我面前。他没有戴面具。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脸。他的脸,很白,
甚至有点苍白。五官很深邃,像雕塑一样。鼻梁很高,嘴唇很薄。他的眼睛,还是那么黑,
那么深。但今天,那双眼睛里,没有了空洞,也没有了疯狂。
是一种……很复杂的、我看不懂的情绪。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很合身,
把他衬得更加清瘦挺拔。那样子,不像一个绑匪,一个杀手。
像要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典礼。他的手里,捧着一束花。不是娇贵的玫瑰,
也不是华丽的百合。是那种,开在山野里的、不知名的小野花。有黄的,有紫的,
还带着清晨的露水。他看着我,把花,递到我面前。我呆住了,不知道该不该接。
他也不说话,就那么举着。手臂很稳。我犹豫了很久,还是伸出手,接过了花。花瓣上,
还带着凉意。“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他开口了。我点点头。“我问过你父亲了。”他说,
“他又拒绝了一次。”我的心,沉了下去。意料之中。“他说,就当我死了。”我的手,
握紧了那束花。顾沉在我面前,单膝跪了下来。我彻底懵了。他抬头看着我,眼睛里,
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灼热的东西。像要把我烧成灰烬。然后,他说出了那句,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既然他们不要你了,”“那以后,”“你就只属于我。
”8地下室里,死一样地安静。只有那盏昏暗的灯,照着我们两个人。他单膝跪在地上,
仰头看着我。手里,没有戒指。只有那双黑得吓人的眼睛。我看着他。
看着这张第一次见到的、苍白又英俊的脸。他说,以后,我只属于他。很可笑。一个绑匪,
对他的肉票求婚。可我,笑不出来。我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有荒唐,有恐惧,有茫然。
还有一丝……被拉住的、落水者般的庆幸。“你……”我张了张嘴,才发现声音抖得厉害,
“你这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他说,“嫁给我。”“我们结婚。”我看着他,
像在看一个怪物。“为什么?”我问。“因为,”他站起来,走到那幅被盖住的画前,
一把掀开了白布。画布上,是我。那个眼神空洞,表情认命的我。“因为,
你是我最好的作品。”他说,“我不能让你毁在别人手里。”“也不能让你自己毁了自己。
”我看着那幅画,又看看他。我明白了。这不是爱。
这是一种……创造者对作品的、极致的占有欲。他不是在向我求婚。他是在给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