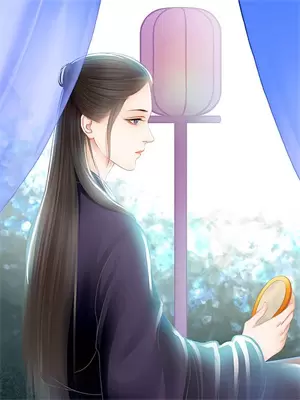1 离奇案子“嗡……嗡……”突如其来的震动声,将我从梦境中拽了出来。我睁开眼,
黑暗中,只有手机屏幕那一点执拗的光,刺得我眼睛生疼。凌晨两点十七分。
看到来电显示是“指挥中心”,我的太阳穴就开始突突直跳。这个时间点的电话,
从来没有好事。“刑侦支队,陈河。”我接起电话,声音因为刚睡醒而显得有些沙哑。
但电话那头确是无法掩饰的惊慌:“陈队!西郊,张家村,发生命案!
情况……情况非常诡异!你最好亲自过来一趟!”诡异?我忍不住笑了笑,
想到当了十年刑警,从支离破碎到面目全非,什么样的“诡异”没见过。“死者什么情况?
报案人是谁?”我一边说,一边已经翻身下床,随手抓过椅子上的衬衫和长裤。
“死者是名女性,在出租屋里被发现的。报案人是她男朋友,叫李伟,现在就在现场,
情绪快崩溃了。但是陈队……现场……现场太他妈邪门了!”电话里,
小王的声音已经开始断断续续,“总之你来就知道了!”挂断电话,我这才算是认真起来,
毕竟能让一向胆大的小王都语无伦次,看来事情确实不简单。三十分钟后,我到达了附近。
当即我便感觉到不对劲!且是非常的不对劲!!张家村以养狗闻名,尤其是村里的刘大壮,
是本市最大的狗肉供应商。按理说,一进村口,此起彼伏的狗叫声就该把人的耳朵给震聋了。
可今晚,村子里的狗就像是病了一样,一个个连叫的力气似乎都没有了!这种反常的安静,
像一块巨石压在我的心口,让我喘不过气来。警灯在村子深处的一栋二层小楼前闪烁,
红蓝交织的光线将周围几名警察的脸照得一片煞白。我推开车门,
一股混杂着泥土和腐败气息的冷风灌了进来。一个年轻人正蹲在警戒线外,抱着头,
身体筛糠似的抖动,嘴里发出意义不明的呜咽。他应该就是报案人李伟。我没有理他,
径直走向那栋小楼。小王看到我,脸色惨白地迎了上来,嘴唇哆嗦着,
指了指二楼的窗户:“陈队……你……你做好心理准备。”我深吸一口气,
踏上吱呀作响的楼梯。越靠近二楼的那个房间,一股奇特的的味道就越发浓郁。
那不是血腥味,倒像是屠宰场里处理牲畜内脏时才会有的味道。法医老徐已经在了,
他戴着口罩和手套,但那双看惯了生死的眼睛里,此刻也写满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他看到我,
只是摇了摇头,示意我自己看。我的目光,投向了房间的正中央。那一瞬间,
我感觉自己的心跳都停止了。当了十年刑警,见过上百具尸体,但我发誓,
我从未见过如此……如此挑战人类认知极限的画面。一个“人”,坐在书桌前。
之所以用引号,是因为那具身体已经不能称之为人。它全身的皮肤,
被人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手段完整地剥离了,
只留下一具覆盖着黄色脂肪和红色肌肉组织的躯体。就像一具被精细处理过的人体解剖标本。
她保持着一个端坐的姿势,一手按着桌上摊开的书,另一只手握着笔,
似乎正在专注地解一道难题。如此一来我很快便发现三件更为恐怖的事情。第一,
现场没有血。一滴都没有。无论是尸体上,还是地面、墙壁,都干净得过分。
似乎她全身的血液都在被剥皮之前,就已经被抽干了。第二,
她体表的毛细血管网络清晰可见,纤毫毕现,但没有一处破裂。
这根本不可能是任何已知的利器能做到的。剥皮,却不伤及一丝一毫的表层血管,
这需要超越人类极限的精准。第三,也是最让我毛骨悚然的是她的“表情”。
尽管已经没有了皮肤和五官,但通过肌肉的走向,你依然能清晰地辨认出,
那是一种极度专注、甚至带着一丝考前焦虑的神情。
无形中好像那件被称为“皮”的衣服只是被她褪去一般。
“呕……”看到最后一个年轻的警员再也忍不住,冲到走廊上大口地呕吐起来。而我,
只是死死地盯着那具红黄相间的标本。我认为这不是简单的谋杀。而更像是在特意展示!
就如一件艺术品。是由用人的血肉和灵魂创作的猎奇艺术品。
2失声的村庄“姓名”“李……李伟。”“职业。”“企业员工。”“死者刘倩,
是你女朋友?”“是……我们……我们都快订婚了……”李伟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他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全是泪水,“警官,求求你们,一定要抓住那个畜生!
倩倩……倩倩她那么好的人,她就想考个研,离开这里……她怎么会……”他说不下去了,
又把头埋进臂弯里,发出压抑的哭嚎。我坐在他对面,手里夹着一支早已熄灭的烟。
审讯室的灯光很白,照得他年轻的脸毫无血色。已经是凌晨四点,
距离发现尸体过去了两个小时,但他身上的颤抖丝毫没有减弱。“最后一个问题,
”我把烟丢到脚下,身体微微前倾,盯着他的眼睛,“今晚,你为什么会突然来找她?
”李伟猛地一颤:“我……我给她打电话,她一直不接。我们说好了的,
她每天晚上学习到十一点半,就会给我打电话聊天……可是今天……我等到快一点了,
电话还是打不通,我……我心里不踏实,就……就骑着电瓶车过来了。
”“她以前有过不接电话的情况吗?”“没有!绝对没有!”李伟斩钉截铁地摇头,
“倩倩很乖的,她知道我担心她。她说好了就一定会做到。”“你到的时候,
门是开着还是锁着?”“锁……锁着的。我用备用钥匙开的门,
…就闻到一股怪味……然后……然后我就看到……看到了……”他的精神显然已经到了极限,
再问下去也问不出什么了。我示意小王将他带去休息室,自己则走进了法医解剖室。
冰冷的解剖室里,老徐正对着那具已经覆盖上白布的尸体发呆。他摘下口罩,
疲惫地揉了揉眉心。“陈河,我干了三十年法医,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专业知识是个笑话。
”“有什么发现?”我问。“发现就是‘没有发现’。”老徐苦笑一声,“死者刘倩,女,
24岁。死亡时间推断在昨晚十点到十一点之间。死因……我他妈的说不上来!
”他猛地一掌砸在了旁边的器械台上。震得连上面的工具都倒了一地。
“全身皮肤被完整剥离,但皮下组织、肌肉、血管,甚至神经末梢都完好无损。
没有任何刀口,没有任何撕裂伤。你知道那像什么吗?”老徐抬起头,
眼睛里闪烁着一种近乎疯狂的光,“就像一条蛇在蜕皮!那层皮是自己‘脱落’下来的,
而不是被外力剥掉的!”蛇蜕皮?我脑子里嗡的一声。这个比喻荒诞,
却又无比精准地描绘了那个场景。“血液呢?”“全身血液消失了大约80%,
但体内和现场都没有找到失血点。就像被什么东西隔空‘吸’走了。更诡异的是,
她体内没有任何毒物残留,没有挣扎的痕迹,各项生命体征在死亡前一秒都还是平稳的。
她就是在最专注、最平静的状态下,被剥了皮,抽干了血,然后死了。”老徐顿了顿,
一字一句地说道:“陈河,从法医学的角度看,杀死她的‘凶手’,
不像是人类能理解的范畴。”走出解剖室,清晨的冷风让我打了个哆嗦。
天边已经泛起了一丝鱼肚白,但我的心里却是一片比深夜更沉重的黑暗。
一个不可能的犯罪现场,一个不存在的凶器,一个无法解释的死因。这个案子,
从一开始就透着一股浓浓的邪气。我决定再去一次张家村。白天的小村庄,
褪去了夜晚的阴森,但那种诡异的死寂却丝毫未减。家家户户门窗紧闭,
路上看不到一个行人。偶尔有窗帘被拉开一道缝,
一双双窥探的眼睛在看到我们身上的警服后,又惊恐地缩了回去。整个村子,
依然听不到一声狗叫。我们找到了村长,一个六十多岁、满脸皱纹的老头。他搓着手,
一脸为难。“警察同志,不是我们不配合……是这事……邪性啊!”村长压低了声音,
眼神惊恐地四下乱瞟,“我们村是养狗的,家家户户都有十几条甚至几十条狗。
可从半个月前开始,村里的狗……就陆陆续续地不出声了。”“不出声了是什么意思?
”小王不解地问。“就是哑巴了!前一天还叫得欢,第二天就跟被人缝了嘴一样,只会呜呜,
喂东西也不吃,就那么趴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村西头的老树那边,浑身发抖。没过两天,
就死了。”村长说着,牙齿都在打颤,“半个月,全村几百条狗,死得就剩下十几条了!
连刘大壮家那几百条狼狗,都死了一大半!”刘大壮?死者刘倩的父亲。“刘大壮人呢?
”我立刻问道。“在他家狗场呢。出了这么大的事,他女儿……唉!”村长叹了口气,
“警察同志,我跟你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们赶紧走吧。
我们村……这是招了不干净的东西了!刘倩那孩子……是被‘那个东西’给收了啊!
”他的话像一盆冰水,给我兜头浇下。我看着村子里家家户户门上贴着的黄纸符,
和窗户上挂着的八卦镜,心里那股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
3:狗肉大户的沉默刘大壮的狗场在村子最西边,紧挨着一片荒山。还没走近,
一股浓烈的腥臊味就扑面而来。巨大的狗场,此刻却安静得像一座坟墓。
一排排空荡荡的铁笼锈迹斑斑,只有零星几个笼子里,还趴着几条瘦骨嶙峋的土狗。
它们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看到我们走近,只是惊恐地往笼子深处缩了缩。
一个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正蹲在地上,用铁锹挖着坑。他身边,
已经堆了七八个黑色的塑料袋,袋子鼓鼓囊囊,渗出暗红色的液体。他就是刘大壮,
死者刘倩的父亲。“刘先生,我们是市刑侦队的。”我走上前,出示了证件。刘大壮抬起头,
看了我们一眼。似乎对于我们的到来,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意外,也没有身为死者家属的悲痛。
只是沉默地,一铲一铲地挖着坑。“你女儿刘倩遇害了,你知道吗?”“知道了。
”他看着地面说,“村长跟我说了。”“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吗?”小王忍不住上前一步,
语气有些激动,“死的是你亲生女儿!”刘大壮挖土的动作停顿了一下。他抬起头,
浑浊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一丝波澜,但那不是悲伤。随即咧开嘴,笑了一下,
“她自己不听话,总想着往外跑,总嫌我这个当爹的丢人……现在好了,跑不掉了,
永远留在这里了。”这番话冷血得让人发指。我皱了皱眉,
压下心头的不适:“我们来是调查案情的。刘倩在村里有没有和人结过仇?”“仇家?
”刘大壮嗤笑一声,指了指周围死气沉沉的狗笼,“我刘大壮靠杀狗卖肉为生,
断了不知道多少人的财路,想我死的人能从村头排到村尾。我女儿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我的仇家,就是她的仇家。”他这番话,看似坦荡,实则把所有线索都堵死了。“村长说,
村里的狗最近死了很多,你家的也是?”我换了个话题。提到狗,
刘大壮的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是。”他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怎么死的?
”“不知道。”“没找兽医看看?”“看了,看不出毛病。”“什么时候开始死的?
”“半个月前。”他的回答像一台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多一个字都没有。这种极度的不配合,
反而让我更加确定,他一定知道些什么。“刘先生,”我加重了语气,“你女儿死状凄惨,
全身皮肤被剥,现场没有一滴血。你觉得,这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吗?
”“皮肤被剥……”刘大壮喃喃地重复着这几个字,眼神里的恐惧几乎要溢出来。
但他还是死死地咬着牙,一个字也不肯多说。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法医老徐。
“陈河!有重大发现!你赶紧回来!”我深深地看了一眼还在挖坑的刘大壮,
和他身边那些散发着不祥气息的黑色塑料袋。“我们还会再来的。”丢下这句话,
我带着小王迅速离开了狗场。在车上,小王愤愤不平地说:“这个刘大壮,简直不是人!
女儿死了他跟没事人一样,肯定有鬼!”我没有说话,
脑子里却在飞速地将所有线索串联起来。一个被完整剥皮、血液消失的女孩。
一个集体失声、离奇死亡的狗群。一个冷漠麻木、讳莫如深的父亲。这三者之间,
一定存在着某种不为人知的联系。刘大壮的沉默,不是因为冷血,而是因为极度的恐惧。
他在害怕,害怕说出那个秘密,会招来比女儿死亡更可怕的后果。回到市局,
我直接冲进了法医中心。老徐正站在一台高倍电子显微镜前,脸色前所未有的凝重。
“你看这个。”他指着屏幕上被放大了数千倍的图像。
那是从死者刘倩皮下组织提取的样本切片。屏幕上,在红色的肌理纤维之间,
附着着一些极其微小的、半透明的物质。“这是什么?”我问。
“一开始我以为是某种细菌或者真菌的残留物,但经过成分分析……”老徐咽了口唾沫,
艰难地说道,“它的蛋白质结构,不属于地球上任何已知的生物。而且,
我们在里面检测到了微量的……消化酶。”“消化酶?”“对。一种活性极强的,
可以瞬间溶解表皮与真皮连接组织的酶。”老徐的声音都在发飘,“陈河,
还记得我之前的比喻吗?蛇蜕皮。现在我告诉你,那不是比喻!”他猛地抬起头,
死死地盯着我,一字一顿地吐出了那个让我浑身血液都几乎凝固的结论:“刘倩的皮肤,
不是被‘剥’下来的,而是被一层覆盖在她体表的、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给‘消化’和‘吸收’了!凶手……或者说那个‘东西’,它把刘倩的皮……给‘吃’了!
”4:山神的契约“它把皮……吃了?”我一瞬间忽然感觉科学不存在了。办公室里,
烟雾缭绕,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头。小王和几个核心队员坐在我对面,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惊骇和茫然。老徐的发现,像一把重锤,
彻底击碎了我们建立在科学和逻辑上的世界观。消化、吸收皮肤的未知生物酶?
这已经不是刑事案件的范畴,这是生物学、甚至神话学的领域。“陈队,这……这怎么查啊?
”小王的声音带着一丝绝望,“总不能让我们去抓个妖怪吧?”“妖怪”两个字一出口,
整个办公室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曾几何时,这是我们用来嘲笑那些封建迷信的老百姓的词,
可现在,它却成了我们唯一能想到的,最贴近真相的解释。我猛地站起身,
将烟头狠狠地按熄在烟灰缸里。“不管它是人是鬼,是妖是魔,它杀了人,就得付出代价!
”我斩钉截铁地说道,“既然科学的道路走不通,我们就走另一条路!
”我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从现在开始,兵分两路。小王,你带人去市图书馆、档案馆,
查阅所有关于张家村以及西郊那片山区的县志、地方传说、民间怪谈,
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要放过!另一组人,跟我再去张家村,这次,我们的目标不是找人,
是找‘东西’!”“找什么东西?”“找那个村长口中‘不干净的东西’!
”再次来到张家村,天色已经擦黑。这次,我没有直接去找刘大壮,
而是找到了那个战战兢兢的村长。我将一份文件拍在他面前的桌子上。“这是市局的封村令,
从现在开始,张家村许进不许出,直到案件查清为止。”我冷冷地看着他,“村长,
我时间有限,耐心也有限。我只问你一次,刘倩的死,还有村里狗的死,到底和什么有关?
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如果你想让整个村子的人,都给你那个所谓的‘秘密’陪葬的话。
”我的话像一把尖刀,刺破了他最后的心理防线。村长一哆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