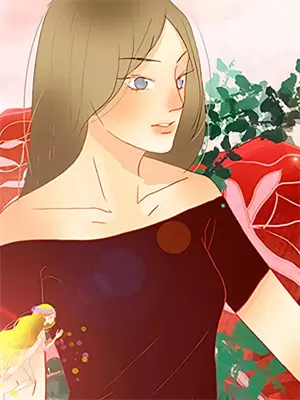
1 血染赤水禹陵以北八十里,赤水河畔的平原上,尸骸枕藉。残阳如血,
将浸透血水的焦土染得更加刺目。破碎的旌旗斜插在泥泞里,半掩着一具年轻士兵的尸体,
他空洞的眼睛望着铅灰色的天空。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汗臭和铁锈的混合气味,
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死亡的沉重。公子启拄着半截折断的长戈,
勉强支撑着自己摇摇欲坠的身体。他那身象征王族血脉的玄色犀皮甲胄,
此刻布满了刀砍斧凿的痕迹,左肩甲更是被生生劈开一道豁口,露出里面被血染红的里衣。
额角一道伤口仍在缓缓渗血,混合着汗水和污泥,蜿蜒而下,糊住了他半边视线。
他剧烈地喘息着,每一次吸气都牵扯着胸腹间翻江倒海的疼痛。环顾四周,
他的心像被一只冰冷的铁手死死攥住——他带来的五千精锐王师,如今还能站着的,
不足百人,个个带伤,眼神里充满了劫后余生的恐惧和难以置信的茫然。就在两个时辰前,
他还在中军大帐里意气风发。父王禹王扫平九夷、划定九州的赫赫威名如同烈阳悬顶,
他是这轮太阳最耀眼的继承者。面对有扈氏这个蕞尔小邦的挑衅,他视若蝼蚁蚁聚。
他兵多将广,装备精良,占据地利,
甚至拒绝了老成持重的副将卫峥提出的分兵试探、稳扎稳打的建议。“区区有扈,跳梁小丑!
何须谨慎?擂鼓!全军突击!一战而定!”他年轻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锐气,拔剑前指。
战鼓擂响,声震四野,王师的铁流带着碾压一切的气势冲向有扈氏那看似单薄的军阵。然而,
那看似一冲即溃的防线,却如同深不见底的泥潭。有扈氏的士兵矮小精悍,
行动迅捷如林间猿猴。他们并不硬撼王师的锋芒,而是利用对地形的极端熟悉,
在看似平坦的河滩上神出鬼没。王师沉重的战车陷入松软的河泥,进退维谷,
成了绝佳的靶子。混乱中,有扈氏伏兵四起,他们如同狡猾的狼群,专攻侧翼和辎重,
精准地切割着王师庞大的阵型。更致命的是,无数涂着毒汁的短小弩矢,
从芦苇丛、土丘后、甚至是从倒毙的马腹下射出,悄无声息地收割着王师士兵的生命。
公子启亲眼看着自己最信任的先锋官,那个曾徒手搏杀过巨熊的勇士,被一支毒矢射中咽喉,
连惨叫都未及发出便栽倒马下。他引以为傲的冲击阵型被彻底打散,指挥系统在混乱中断裂,
士兵们各自为战,很快陷入了被分割包围、逐一歼灭的绝境。“公子!快走!
”一声嘶哑的咆哮在耳边炸响。副将卫峥浑身浴血,如同地狱归来的恶鬼,
猛地撞开两个扑向公子启的有扈氏士兵,他的左腿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扭曲着,显然已断。
“末将断后!走啊!”公子启被几个亲卫死命拖拽着向后撤。卫峥拄着长戟,
仅靠一条腿站立,对着汹涌而来的敌兵发出最后的怒吼,
那背影在血色残阳中悲壮得令人窒息。公子启最后看到的,是卫峥被数支长矛同时贯穿身体,
轰然倒地的画面。耻辱!前所未有的耻辱!像滚烫的岩浆,灼烧着他的五脏六腑,
几乎要将他吞噬。败兵如退潮般涌回禹陵城。沉重的城门在身后轰然关闭,
隔绝了平原上地狱般的景象,却关不住那弥漫在空气中的血腥味和浓得化不开的失败气息。
城头上,守军士兵的目光不再是往日的敬畏,而是掺杂着惊疑、恐惧,
甚至……一丝不易察觉的鄙夷。公子启没有回王宫,甚至没有去处理肩头的伤口。
他像一具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拖着沉重的步伐,径直走向禹陵城西侧的宗庙。
夕阳的余晖将宗庙高耸的檐角染成凄厉的金红色,如同凝固的血块。
沉重的石门在他身后缓缓合拢,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喧嚣与目光。宗庙内光线幽暗,
唯有长明灯豆大的火苗在青铜灯盏里跳跃,映照着墙壁上历代禹王征伐四方的壁画,
那些开疆拓土的先祖目光炯炯,仿佛穿透时空,冷冷地注视着他这个不肖子孙。
正中供奉着禹王治水时开山裂石所用的巨大玄圭,黝黑冰冷,散发着沉重的威压。“噗通!
”公子启双膝重重砸在冰冷的青石地面上,膝盖骨碎裂般的疼痛远不及心头的万分之一。
他深深俯首,额头紧贴着粗糙的石板,冰冷的触感直刺骨髓。
肩膀的伤口因这剧烈的动作再次崩裂,温热的鲜血顺着甲胄的缝隙渗出,
滴落在身下的石板上,发出轻微的“嗒、嗒”声,在这死寂的宗庙里格外清晰。
父王禹王威严的面容在他混乱的脑海中浮现。他曾亲授自己《洪范九畴》,讲述“王道荡荡,
无偏无党”的治国大道;他曾指着九州贡图,谆谆告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民心即天命!”可自己呢?自己都做了什么?骄狂!自大!视有扈如草芥,拒忠言于千里!
将五千忠勇将士的性命,如同儿戏般葬送在那片血染的河滩!卫峥那扭曲的腿,
那最后悲壮的怒吼,如同烧红的烙铁,反复烫在他的灵魂上。
“父王……列祖列宗……”他喉咙里发出野兽受伤般的呜咽,声音嘶哑破碎,
在空旷的宗庙里激起空洞的回响,“启……有罪!启……无能!启……愧对祖宗基业!
愧对……五千亡魂!”滚烫的泪水终于冲破堤坝,混合着额头的血水,汹涌而下,
灼烫着他冰冷的脸颊,滴落在身下的青石板上,与血渍混在一起。
“兵多……地广……”他喃喃着战前那狂妄的宣言,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钝刀在切割自己的心,
“却……一败涂地……一败涂地啊……”他猛地抬起头,
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壁画上先祖开疆拓土的雄姿,又缓缓移向那柄象征无上权柄的玄圭,
一种前所未有的彻悟,如同冰冷的雪水,浇灭了所有的狂躁与不甘。“非兵不利!非地不广!
”他对着幽暗的虚空,对着那些无声的先祖牌位,一字一顿,如同用尽全身力气刻下血誓,
“是启……德薄能鲜!刚愎自用!御下无方!是我……是我自己……不如人!
”声音在宗庙的梁柱间回荡,带着绝望的清醒和彻骨的痛悔。这一刻,
那个骄傲不可一世的王位继承人彻底死去,跪在这里的,
是一个被失败剥去所有光环、直面自身丑陋与虚妄的罪人。2 断发立誓不知跪了多久,
直到长明灯的灯油快要燃尽,灯火变得飘摇不定。宗庙沉重的石门被无声地推开一道缝隙,
一个身影悄然而入,脚步轻得如同猫。是公子启的母亲,虞夫人。她没有穿华丽的宫装,
只着一件素净的深青色常服,发髻间仅簪着一支样式古朴的玉簪。
她手中捧着一只粗糙的陶碗,碗口冒着丝丝热气。看到儿子如同血人般跪伏在地,背影佝偻,
肩膀微微颤抖,虞夫人眼中瞬间蓄满了泪水,但她强忍着没有落下,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她默默走到公子启身后,将温热的陶碗轻轻放在他身侧的地上。碗里是熬得浓稠的小米粥,
散发着朴素而温暖的谷物香气。然后,她伸出微凉而柔软的手,极其轻柔地,
试图去触碰儿子肩上那道狰狞的伤口。“母亲……”公子启身体猛地一颤,没有回头,
声音沙哑干涩,“别……脏……”他下意识地想躲开那温柔的触碰,仿佛自己不配。
虞夫人的手顿在半空,泪水终于无声滑落。她没有强行触碰伤口,
只是用那温柔而坚定的声音,低低地说道:“启儿,伤口……总要清理的。先喝口热粥吧,
暖一暖身子。”她的声音带着一种奇异的安抚力量,穿透了公子启心中厚重的绝望壁垒。
公子启缓缓转过头。火光映照下,他脸上的血污和泪痕交织,狼狈不堪,
但那双原本被狂怒和恐惧占据的眼睛,此刻却沉淀出一种死寂般的平静,
以及一种近乎残忍的清明。他看着母亲担忧的泪眼,
又看了看地上那碗冒着热气的、最普通不过的小米粥,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猛地涌上喉头。
他颤抖着伸出手,不是去端碗,而是猛地抓住了自己束发的玉冠!那玉冠由整块青玉雕琢,
温润华美,是王族身份的象征。他眼中闪过一丝决绝的厉色,五指狠狠收拢!“咔嚓!
”一声清脆刺耳的碎裂声在幽静的宗庙里骤然响起!价值连城的青玉发冠,竟被他生生捏碎!
碎裂的玉片割破了他的掌心,鲜血瞬间涌出,滴落在青石板上,与之前的血泪混在一起,
触目惊心。虞夫人惊呼一声,捂住了嘴。公子启却仿佛感觉不到掌心的疼痛。
他摊开鲜血淋漓的手,任由那些带着棱角的碎玉跌落在地,发出细碎的声响。然后,
他看也没看,用那只染血的手,胡乱地、粗暴地将自己散乱的黑发向后捋去,
露出光洁而苍白的额头。“从今日起,”他看着母亲,声音不高,
却带着一种斩断一切过去的金石之音,字字如刀刻入骨髓,“凡衣食享用,
皆与城中戍卒、百姓无异!启,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公子,只是一个……待罪之身!
”他端起地上那碗还烫手的小米粥,滚烫的陶壁灼痛了他掌心的伤口,他却浑然不觉。
他低下头,凑近碗边,没有用汤匙,就那样大口大口地、近乎贪婪地吞咽起来。
滚烫的粥水滑过干涩疼痛的喉咙,粗糙的米粒摩擦着食道,
带来一种真实的、近乎自虐的灼痛感。他吃得很快,很急,
仿佛要将这份粗粝的痛楚连同那深入骨髓的耻辱,一同吞咽下去,刻进自己的生命里。
虞夫人看着儿子狼吞虎咽的样子,看着他额角未干的泪痕与血污,
看着他掌心淋漓的鲜血滴落在粗陶碗沿,看着他眼中那份破釜沉舟的决绝,
泪水无声地汹涌而出。她没有劝阻,只是默默地、更深地躬下身,用一方素净的丝帕,
极其轻柔地,试图包裹住儿子那只不断滴血的手掌。冰冷的丝帕触碰到伤口,
带来一阵尖锐的刺痛。公子启吞咽的动作顿了一下,他抬起眼,看向母亲。
母亲眼中的泪水滚烫,却带着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深沉的理解与无言的支撑。那一刻,
宗庙内先祖的目光仿佛不再冰冷,那柄玄圭的威压也似乎不再沉重。他猛地低下头,
将脸深深埋进粗糙的陶碗边缘,肩膀剧烈地耸动起来,压抑的呜咽混合着吞咽的声音,
在空旷的宗庙里久久回荡。这一次的泪水,不再仅仅是悔恨,
更混杂着一种破茧重生般的痛楚与一丝渺茫的、沉重的希望。3 开仓赈民翌日清晨,
天刚蒙蒙亮,禹陵城的百姓便被一阵不同寻常的动静惊醒。
往日紧闭森严、由精锐王宫卫队把守的公子府邸,那两扇厚重的朱漆大门,此刻竟大敞四开!
门前的空地上,密密麻麻堆积着小山般的物品。在初秋微凉的晨光中,
闪烁着令人目眩神迷又心惊肉跳的光泽。成箱成箱的丝绸锦缎,色彩斑斓如云霞,
此刻却被随意地堆叠挤压着;堆积如山的精米白面,
散发出诱人的谷物香气;整扇整扇风干的鹿肉、腊肉,
油脂在晨光下泛着暗红的光;还有那些沉重的青铜礼器,造型古朴,纹饰繁复,
象征着无上的权力与地位,
;更别提那些码放整齐的、沉甸甸的皮口袋——里面装满了金灿灿的饼金和打磨光滑的贝币,
那是足以让任何平民家族几世无忧的财富!人群越聚越多,窃窃私语声如同潮水般蔓延开来,
充满了惊疑、不解和一丝隐秘的兴奋。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府邸大门内那个缓步走出的身影上。公子启。
他换下了那身象征王族身份的玄色犀皮甲胄,仅穿着一套最普通的麻布深衣,
浆洗得有些发白,袖口和下摆甚至还带着磨损的毛边。
他的头发用一根最寻常的麻绳随意束在脑后,额角那道伤口已简单处理过,
贴着一小块干净的葛布。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双眼睛,
昨日还充斥着狂怒与绝望的血丝已经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枯井般的沉静,沉静之下,
是深不见底的疲惫与一种令人心悸的决绝。他走到那堆积如山的财货前,
目光平静地扫过人群那一张张惊愕、猜疑、甚至带着贪婪的面孔。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清晨微凉的空气带着露水的湿意涌入肺腑。“父老乡亲们!”他的声音不高,
却清晰地穿透了嘈杂的人声,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瞬间让全场安静下来。
无数道目光聚焦在他身上。公子启抬起手,指向身后那堆积如山的财货,
每一个字都说得异常清晰、沉重:“这些,
帛、粟、肉、金、贝……乃至府中所有逾制奢靡之物,皆非启一人之力所能聚敛!
皆取之于民脂民膏!”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痛切的忏悔,“昨日赤水河畔,
五千忠勇王师将士,因启一人之骄狂昏聩,葬身异域!此滔天之罪,百死莫赎!
”人群一片死寂,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赤水惨败的消息早已传回,
但亲耳听到这位高高在上的公子如此赤裸裸地承认自己的罪责,
甚至用“骄狂昏聩”来形容自己,所带来的震撼依旧如同惊雷炸响在每个人心头。
那些堆成山的财货,此刻在众人眼中,仿佛染上了牺牲将士的血色。“启,愧对祖宗!
愧对父王!愧对禹陵城每一位将子弟托付于我的父老!更愧对……那些埋骨他乡的英魂!
”公子启的声音微微发颤,他顿了顿,似乎在极力压抑翻腾的情绪,目光扫过人群,
最终定格在几个穿着破旧、脸上带着菜色的老农身上。“自今日起,启府中所有存粮、肉脯,
尽数开仓!”他斩钉截铁,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城中凡孤寡老弱、家无隔夜之粮者,
皆可凭里正手书,前来领取粟米三斗,肉脯两斤!直至仓空!”人群轰然骚动起来!
惊愕瞬间被巨大的狂喜和难以置信所取代!那些面黄肌瘦的贫苦百姓,
眼中迸发出难以置信的光芒,激动得浑身发抖。“府中所有丝帛锦缎,
”公子启的声音继续响起,压下了喧哗,“尽数裁为冬衣!由府中仆妇日夜赶制,
务必在霜降之前,分发至城中戍卒家眷、孤寡老弱手中,以御寒冬!
”“府中所有金、贝、礼器,”他指向那堆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令人炫目的财富,
“尽数变卖!所得钱资,一半抚恤赤水河畔阵亡将士遗属!另一半……”他深吸一口气,
声音更加凝重,“悉数用于加固禹陵城防!修葺武库!打造兵甲!招募敢战之士!”“轰!
”人群彻底沸腾了!如果说之前的开仓放粮是恩泽,
那么这变卖府库、抚恤遗孤、加固城防的举动,则带着一种破釜沉舟、与城共存的决绝!
无数道目光再次投向公子启,那眼神中的惊疑、贪婪迅速消退,
取而代之的是震惊、是动容、是难以置信的复杂情绪。
“公子……”人群中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颤巍巍地开口,声音哽咽,“使不得啊!
这……这都是……”公子启抬手,制止了老者的话。他环视众人,目光沉静如水,
却又蕴含着千钧之力:“启非施恩,实乃赎罪!此身此心,此城此民,自今日起,一体同休!
启,在此立誓——”他猛地拔出腰间那柄装饰意义大于实战的佩剑,剑身寒光一闪!
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他竟挥剑猛地斩向自己垂落的一缕鬓发!青丝断落,飘散在晨风中。
“若再有负于民,有负于国,有负于牺牲将士之英灵!”公子启的声音如同金铁交鸣,
掷地有声,“犹如此发!天地共弃!人神共诛!”断发飘落尘埃。整个禹陵城门前,
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唯有公子启那沉静而决绝的目光,如同磐石,烙印在每一个人的心底。
4 血债血偿禹陵城西,靠近城墙根的地方,有一大片低洼的棚户区。这里污水横流,
空气中常年弥漫着腐烂垃圾和劣质炭火的味道。歪歪扭扭的窝棚如同雨后滋生的毒蘑菇,
紧紧挤挨在一起。
老兵、无力承担城内高昂租税的苦力、以及那些在赤水之战中失去了家中顶梁柱的孤儿寡母。
卫峥的家就在这片棚户区最深、最潮湿的一个角落。
窝棚是用捡来的破木板和废弃的草席勉强搭成,四面漏风。
公子启推开那扇吱呀作响、形同虚设的破木门时,
一股浓烈的草药味和一种破败衰朽的气息扑面而来。光线昏暗。
卫峥躺在角落一堆散发着霉味的稻草上,身上盖着一件千疮百孔的旧军袄。
他原本健硕的身体如今瘦得脱了形,脸颊深陷,颧骨高耸,嘴唇干裂起皮。
最触目惊心的是他的左腿——膝盖以下空荡荡的,断口处包裹着肮脏的、渗着黄水的布条。
苍蝇嗡嗡地围着那伤口打转。一个头发枯黄、面有菜色的小女孩,大约五六岁,
正用一块破布蘸着瓦罐里浑浊的水,试图给父亲擦拭额头滚烫的汗水。
“阿爹……喝水……”小女孩的声音怯生生的,带着哭腔。卫峥紧闭着眼,
眉头痛苦地拧在一起,嘴唇翕动着,发出模糊不清的呓语,显然已陷入高热的昏迷。
眼前这一幕,如同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公子启的心上!
比战场上看到卫峥被长矛贯穿时更让他痛彻心扉!卫峥是为救他而断后,
是为救他而落得如此境地!而他,这位高高在上的公子,这些日子忙于“改过自新”,
竟从未想过,或者说,下意识地逃避去想,这位救命恩人、这位忠诚的部将,
在战后是如何挣扎在生死线上,他的家人又过着怎样地狱般的生活!
巨大的愧疚如同冰冷的潮水将他淹没,几乎窒息。他身后的亲随想要上前,
被他一个凌厉的眼神制止。公子启一步步走到草铺前,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他蹲下身,
不顾那污秽的地面和刺鼻的气味。小女孩惊恐地看着这个穿着虽然朴素但气质迥异的陌生人,
下意识地往父亲身边缩了缩。“别怕,”公子启尽量放柔了声音,
但那声音依旧带着沙哑的沉重。他伸出手,没有去碰卫峥,
而是极其自然地接过小女孩手中那块又脏又破的布巾。“去打盆干净的清水来,要烧开的,
温的。”他对身后的亲随低声吩咐。亲随愣了一下,立刻转身出去。公子启就着昏暗的光线,
仔细看着卫峥腿上的伤口。布条下,皮肉翻卷,溃烂流脓,恶臭难闻。他眉头紧锁,
眼中是沉痛的自责。他小心翼翼地解开那污秽的布条,动作尽量轻柔。腐烂的皮肉暴露出来,
引来更多苍蝇。小女孩吓得捂住了眼睛。亲随很快端来一盆温热的清水。
公子启将那块破布在清水中浸湿、拧干。他跪坐在污秽的草铺旁,用这块湿布,
极其细致、极其轻柔地,开始为卫峥擦拭额头、脖颈、手臂上的汗水和污垢。
他避开溃烂的伤口,只清理其他部位。那专注而沉稳的动作,那毫无嫌恶的神情,
仿佛他擦拭的不是一个浑身脏污、散发着恶臭的伤兵,而是一件稀世的珍宝。
小女孩从指缝里偷偷看着,眼中的惊恐慢慢褪去,变成了茫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依赖。
清理完身体,公子启从怀中取出一个油纸包。这是他离府时特意带上的,
里面是上好的金疮药粉和干净的细白麻布。他示意亲随帮忙,两人合力,
极其小心地处理着卫峥腿上的溃烂伤口。剜去腐肉时,昏迷中的卫峥发出痛苦的呻吟,
身体剧烈抽搐。公子启紧紧按住他,额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动作却稳如磐石。
清洗、上药、包扎……每一个步骤他都亲力亲为,
神情专注得如同在进行一场关乎生死的仪式。窝棚里恶臭弥漫,苍蝇依旧在耳边嗡嗡作响,
但他恍若未闻。直到将卫峥的伤口重新用干净的白麻布妥帖地包扎好,他才长长吁了一口气,
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他转头看向一直怯生生躲在旁边的小女孩,
声音异常温和:“你叫什么名字?”“小……小芽……”小女孩细声回答。公子启伸出手,
轻轻摸了摸小芽枯黄的头发,动作有些生涩,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暖意:“小芽,别怕。
以后,不会再饿肚子了。”他解下自己腰间一个并不起眼的粗布小袋,
里面装着几块硬邦邦的、用杂粮和豆子做成的干饼——这是他府中“与戍卒同食”的伙食。
他将整个袋子都塞进小芽冰凉的小手里。“先吃着。很快会有人送米面肉菜来。”他顿了顿,
目光扫过这个四面漏风、摇摇欲坠的窝棚,语气斩钉截铁,“这房子不能住了。我会安排人,
立刻给你们父女,还有这附近所有阵亡将士的遗属、伤残的袍泽,另寻干净温暖的住所!
”小芽紧紧攥着那个粗布袋子,感受着里面食物的坚硬触感,
又抬头看看公子启那张虽然疲惫却异常坚定的脸,懵懂的大眼睛里,
第一次涌上了大颗大颗的泪水,不是害怕,而是一种迟来的、不知所措的委屈和依赖。
就在公子启准备起身离开,去着手安排迁移事宜时,
昏迷中的卫峥突然发出一声含糊的呓语:“公子……快走……”公子启的身体猛地僵住。











